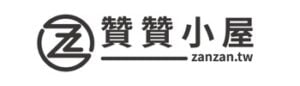(小說)三年後的妻子1:這些年都是怎麼解決?
打工三年,第一次踏進家門,那股混合著洗潔精和米飯溫熱氣息的熟悉味道撲面而來,竟讓他鼻腔有些發酸。小白把沉重的行李包丟在玄關,聲音驚動了廚房裡的人。

妻子繫著那條有點褪色的碎花圍裙,手裡還拿著鍋鏟,從廚房探出頭來。光線從她背後照過來,勾勒出一個柔和的剪影。「回來啦?」她笑著,眼角漾開細細的紋路。
小白「嗯」了一聲,走過去,想抱抱她,又覺得身上汗津津的,動作便有些遲滯。妻子似乎也頓了一下,然後自然地轉身回了廚房,「路上累了吧?先歇會兒,飯馬上好。」
晚飯是尋常的家常菜,味道……是記憶裡的味道。兩人面對面坐著,問些路上的情形,說些村裡最近的閒話,聲音填滿了安靜的飯廳,卻又好像隔著一層無形的膜。大概是太久沒見,生分了?小白心裡掠過一絲模糊的念頭,像水底的暗流,悄無聲息。
飯後,他靠在廚房門框上,看著妻子收拾碗筷,水流嘩嘩作響。她動作利落,擦乾手,從刀架上抽出那把最常用的切菜刀,又從籃子裡拿了個土豆,就著流理台削皮,然後切絲。篤篤篤,刀尖急促地敲擊著木板。小白看著那起落的右手,心裡那點模糊的不對勁又冒了出來,像一根極細的刺,扎了一下。是了,她慣用左手,切菜、寫字,一直都是左手。怎麼現在……
他沒問出口。那念頭太荒唐。
「我去下廁所。」他說著,轉身離開了廚房。
妻子沒一會兒也跟了過來,靠在廁所門外的牆上,繼續和他閒聊。說隔壁張嬸家的孫子會滿地爬了,說前頭李叔家新買的拖拉機聲音真響。話語像溫水一樣流淌,試圖熨平某種看不見的褶皺。
然後,毫無預兆地,在那片瑣碎的閒聊背景音裡,她突然插進一句:「……你在外頭這幾年,都是怎麼解決的?」
聲音不高,語調甚至沒什麼起伏。
小白愣住了,側過頭看她。她依舊靠著牆,目光卻垂下去,落在瓷磚地板的某條縫隙上,沒有看他。問題的內容直接得近乎粗魯,完全不是他記憶中妻子會問出口的話。她對於這類私密乃至有些隱晦的話題,向來是點到即止,帶著一種天生的靦腆。
「什麼怎麼解決?」他下意識地反問,心裡那根刺又動了動。
「就……男人的需要啊。」她依舊沒抬頭,聲音輕了些,手指無意識地捲著圍裙的帶子。
一股極其輕微的麻癢感,順著他的脊椎爬上來。不對勁。非常不對勁。
「……能怎麼解決,忙都忙死了。」他含糊地應了一句,藉口尿急,閃身進了廁所,反手「咔噠」一聲鎖上了門。
隔絕了外面的聲音,也隔絕了那讓他莫名發毛的視線。狹小的空間裡只剩下他自己有些粗重的呼吸。他靠在冰冷的瓷磚牆面上,心臟在胸腔裡咚咚撞擊。冷靜點,他想,也許只是太久沒見,也許是她聽了什麼閒話,或者……只是隨口一問?
他走到馬桶邊,解開褲子,目光無意識地掃過馬桶潔白的陶瓷邊緣。靠近地面連接處的陰影裡,有一小塊顏色不太對。他皺眉,彎下腰湊近了看。是一小塊淤青,暗紅色裡透著點紫,極小,極淡,像是被什麼重物極其輕微地磕碰過,不仔細看根本發現不了。這馬桶是硬質陶瓷,怎麼會磕出這種顏色的淤痕?倒像是……某種活物的皮膚底下滲出的血點。
左撇子……右手切菜……不合時宜的問題……馬桶邊緣詭異的淤青……
幾個碎片在他腦子裡瘋狂旋轉,碰撞,試圖拼湊出一個他不敢去觸碰的圖景。寒意從腳底猛地竄起,瞬間凍結了四肢百骸。
篤,篤篤。
輕柔的叩門聲響起。
「老公?」門外傳來妻子一如既往溫和的聲音,「怎麼那麼久還不出來?沒事吧?」
他渾身一顫,幾乎能想像出她此刻就貼在門板上,耳朵朝著裡面的樣子。
「沒……沒事!」他急忙應道,聲音因為緊張而有些發緊。他踉蹌著走到洗手台前,猛地擰開了水龍頭。
冰冷的水嘩啦啦地衝擊著瓷盆,發出巨大的聲響,蓋過了他如擂鼓的心跳,也蓋過了門外可能的動靜。他雙手撐著冰涼的台面,大口喘著氣,試圖平復幾乎要炸開的胸腔。
就在這片喧囂的水聲掩蓋之下,一絲極其微弱、彷彿錯覺般的低語,像冰冷的細絲,鑽透門縫,鑽透水聲,鑽進了他的耳膜。
「……應該……沒發現吧……」
聲音頓了頓,帶著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審視意味。
「……這個複製體的……瑕疵……」
水聲還在嘩嘩作響。
小白僵在原地,撐在洗手台上的手指,指甲因為用力而失去了血色。鏡子裡,映出一張慘白、佈滿冷汗、因極度恐懼而扭曲的臉。
那張臉,彷彿也不再是他自己的了。
贊贊小屋小說作品集:
三十年耳鳴、紅衣還願、大太陽奇遇記、未來列車、三年後的妻子。

相關文章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