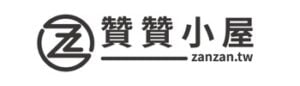(小說)三十年耳鳴1:手術之後,一切都很安靜
手術結束後,我以為一切都回到了正常。耳朵乾燥、安靜,像一段已經被妥善收尾的往事。直到某個夜晚,在世界完全靜下來的時候,我第一次發現,安靜本身,原來也會出錯。

一、童年的那次洗澡
那個塑膠腳桶是紅色的,邊緣有些泛白。母親把熱水倒進去,又用橡皮水管接了冷水調溫。水柱從水管口噴出來時,發出咻咻的聲響,像某種輕微的嘆息。
我坐在小板凳上,低頭。母親說頭髮要沖乾淨,泡沫不能留。她捏著水管,讓水對準我的頭頂。然後——也許是手滑,也許是角度——那股水柱忽然就轉了向,直直衝進我的右耳。
那是一種被填滿的感覺。溫熱,有壓力,但並不特別痛。我縮了一下,母親立刻移開水管,說了聲「哎唷」。她用手指擦了擦我的耳廓,問:「會痛嗎?」
我搖頭。
真的不痛。只是覺得耳朵裡好像塞了什麼,世界變得不一樣——一邊清晰,一邊悶著。我們繼續洗澡,像什麼也沒發生。
後來的事是慢慢來的。先是耳朵有些癢,然後開始流出透明的液體,接著是黃色的膿。醫生說是中耳炎,開了藥,囑咐不要讓耳朵進水。但炎症反覆來,像一個不願離開的客人。耳朵開始有味道,一種淡淡的、甜膩的腐敗氣味。
我學會在睡前塞一小團棉花。早晨取出時,棉花是濕的,顏色從淺黃到褐色都有。上學時我總擔心別人聞到那個味道,所以總是微微側著左臉。沒有人問過。也許他們聞到了但沒說,也許根本沒人在意。耳朵成了一個需要小心對待的部位,像一件易碎的瓷器,得時刻記得它在那裡,記得它與眾不同。
二、醫生的解決方案
時間過去,症狀沒有好,也沒有更壞。它成了一個背景音,一種身體的常態。我學會在洗頭時用手掌緊緊蓋住右耳,學會不用右側臥睡,學會在別人靠得太近時不著痕跡地拉開距離。
耳朵等於弱點。不是那種戲劇性的、會引發憐憫的弱點,而是更私密、更恆常的一種——你必須隨時記得它,因為它不會提醒你,只會在疏忽時懲罰你。
大學時,我去游泳。在水裡一切正常,但上岸幾小時後,右耳開始劇痛。那是一種尖銳的、往腦子裡鑽的痛。我躺在床上,覺得半個頭顱都要裂開。
第二天去看醫生,他用了耳鏡,沉默了一會兒。
「鼓膜破了,」他說,「有一個穿孔。你看這裡。」
他把螢幕轉向我。黑白影像裡,我的耳道深處,有一個不規則的缺口。
「需要手術修補,」醫生說,「耳膜成形術。不算複雜,成功率很高。」
我盯著那個缺口看。它很小,像被針扎破的紙。
「手術後,」醫生繼續說,「就不會再反覆感染了。聽力也可能改善。」
走出診間時,我站在醫院走廊,陽光從盡頭的窗戶斜斜照進來。空氣裡有消毒水的味道。我第一次感覺到——不是希望,是某種更輕的東西,像一片羽毛終於要落地。
這件事可能真的可以結束。
三、哥哥付手術費用
哥哥那時已經在工作了。他在電話裡聽我說完,沉默了幾秒。
「要多少?」他問。
我說了一個數字。他又沉默了一會兒,然後說:「我想辦法。」
手術安排在兩週後。哥哥從外地回來,陪我辦住院。他帶了一個信封,裡面是現金。我沒問他怎麼湊的,他也沒說。我們只是坐在病房裡,看窗外其他大樓的窗戶反射著夕陽。
「媽知道嗎?」他問。
「還沒說。」我說。
他點點頭。「等做完再說吧。」
手術前一天,醫生來做最後說明。他講了手術流程:取一小塊筋膜補穿孔,全身麻醉,大約兩小時。成功率九成以上,但需要長期追蹤,確保癒合良好。
「最重要的是術後回診,」醫生強調,「一定要按時回來,我們要看恢復情況。」
我點頭。哥哥在旁邊也點頭。
那天晚上,哥哥留在醫院陪我。我們沒說什麼話,只是各自滑手機,偶爾聊兩句無關緊要的事。睡前,他忽然說:
「這不是你一個人的事。」
我轉頭看他。
「我的意思是,」他繼續說,眼睛看著天花板,「我們都在這條船上。所以好好做,好好恢復。不要隨便放棄。」
我說好。
然後燈就關了。
四、永遠錯過的回診
手術本身沒有記憶。麻醉就像被刪除了一段時間。醒來時已在恢復室,右耳裹著厚厚的紗布,不痛,只是悶。住院三天,換了幾次藥,然後就出院了。
哥哥送我到車站。他還要回去工作。
「記得回診,」他說,「一個月後,對吧?」
「對。」我說。
「一定要去。」
「好。」
我回到高雄,開始暑假生活。耳朵沒有再流膿,沒有異味,聽東西似乎清楚了一些。一個月後,我回診了一次。醫生說恢復良好,但還要繼續觀察,約了三個月後再回來。
三個月後,我沒有去。
不是故意不去。只是那天早上醒來,覺得耳朵很好,不痛不癢,天氣很好,生活也很好。我想,既然沒有不舒服,就不需要再回去了吧。
醫生應該很忙,有很多真正需要他的人。而我,我已經好了。
暑假結束,新學期開始。我搬進宿舍,認識新的人,上新的課。耳朵漸漸不再是需要時刻關注的部位。洗澡時我不再刻意遮擋右耳,睡覺時可以任意側臥,和人說話時不再擔心距離。
它變成了一個普通的器官,和其他所有器官一樣,安靜地履行職責,不刷存在感。
我以為,既然沒有不舒服,就不需要再回去了。
五、我以為全好了
時間過去得很快,快到你幾乎感覺不到它在走。幾個月變成半年,半年變成一年。耳朵沒有再出過問題。偶爾我會想起手術,想起那個穿孔的影像,但那些都像上輩子的事。
生活繼續。我交朋友,熬夜趕報告,在社團打發時間,煩惱一些年輕人都煩惱的事。耳朵的歷史像一本合起來的書,被放在記憶書架的最深處,落了一層薄薄的灰。
一切看起來都像圓滿落幕。問題出現,醫療介入,問題解決。一個標準的、現代醫學的小勝利。
有時候,在極安靜的夜裡,我會下意識地、像確認一個已知的傷口是否癒合那樣,去感受右耳。沒有濕潤感,沒有隱痛,沒有那種熟悉的、需要小心翼翼對待的脆弱。它乾燥、平靜,彷彿從未出過問題。這是一種陌生的、近乎奢侈的正常。
我甚至開始懷疑,手術前的那麼多年,是不是其實也沒有那麼嚴重?記憶會不會把痛苦誇大了?人總是這樣,好了傷疤,就覺得傷口從來沒那麼深。
耳朵的困擾,正式從我的生活中退役。我以為,困擾的形態是固定的,而我已經歷經了它所有的模樣。
六、那個聲音出現
那天晚上,宿舍很安靜。室友都睡了,發出均勻的呼吸聲。窗外有遠處的車聲,偶爾一聲狗吠,這些聲音都很清晰,從左耳進來,乾乾淨淨的。
我閉著眼睛,快要睡著。
然後,那個聲音出現了。
不是突然爆發,不是轟鳴,不是任何戲劇性的方式。它只是——存在。像有人輕輕扭開了一個開關,有一個聲音開始播放,而且不打算停止。
那是一個高頻的、穩定的聲音。像電視沒有訊號時的尖嘯,但更細、更持續。它不在外面,不在房間裡,它就在我的耳朵裡,或者說,在我的頭裡。
我睜開眼。世界還是那個世界,室友還在睡,車聲還在遠處。但現在,這些聲音的底下,多了一層底噪。一層永遠不會消失的、屬於我自己的聲音。
我坐起來,搖了搖頭。聲音還在。
我按住右耳。聲音還在。
我走到浴室,開水龍頭。水流聲蓋過了一些,但當我關上水,那個聲音又回來了,堅定地、忠實地在那裡。
我回到床上,躺下。那一刻我還不知道,這不是暫時的副作用。
我只是第一次意識到,原來安靜,也會出錯。
而那個錯誤,正從我的頭顱內部,發出永恆的尖嘯。
(第一集結束)
贊贊小屋小說作品集:
三十年耳鳴、紅衣還願、大太陽奇遇記、未來列車、三年後的妻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