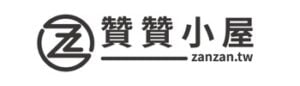(小說)三十年耳鳴2:被判終身監禁,刑期未定
耳鳴沒有消失,我查資料,發現可怕的不是現在,而是未來。醫學說它無法根治,還可能隨年齡加重。那一刻我明白,不是生病,是被提前判了終身監禁。

一、習慣成為日常
耳鳴出現後的第二週,我發現了它的作息規律。
白天,當我騎著摩托車穿梭在台北的街道,風聲和引擎的轟鳴會蓋過它。那一刻,我幾乎是正常的——噪音對抗噪音,世界勉強平衡。我會故意繞遠路,讓通勤時間拉長十分鐘,只為了延長這段偽裝的安寧。
但夜晚是它的領地。
宿舍十一點熄燈後,世界一層層安靜下來。先是走廊的腳步聲消失,然後是隔壁房間的音樂停止,最後連窗外遠處的車流都變得稀疏。每安靜一層,耳鳴就清晰一分。它不是逐漸增強,而是原本被掩蓋的部分逐漸裸露,像退潮後顯露的礁石。
我開始無意識地改變生活。
不再去後山那個可以眺望台北夜景的山坡——那裡的安靜太純粹,純粹到只剩下風聲和它。不再在圖書館待到閉館——最後半小時,人潮散去,翻書聲消失,它就會準時登場。我甚至開始害怕洗澡,因為淋浴的水聲停下那一刻,從喧囂跌入寂靜的落差,會讓它顯得格外刺耳。
和我同系、關係不錯的同學李信妤有一次發現我精神不濟,問:「你最近好像睡得不好?」
我說:「有點失眠。」
她沒再追問。我鬆了一口氣,同時感到某種難以形容的孤獨——那種明明被關心,卻無法說出真相的隔閡。我開始在對話中分神,不是因為不專心,而是因為要分出一部分注意力去確認——它還在嗎?它有多大聲?我有沒有在皺眉?
一個月過去的某個晚上,我躺在黑暗中,聽著那永恆的高頻嘶聲,忽然意識到:我已經開始習慣了。
不是習慣「它會消失」,而是習慣「它不會消失」。
這個認知出現得平靜無波,像確認一個早就知道的事實。那一刻,我心裡某個開關被扳動了。
從「怎麼辦」轉向了「我得想辦法」。
二、我決定戰鬥了
我掛了耳鼻喉科的門診。不是當初動手術的林醫師,是另一位年輕的醫生。
診間裡,他用耳鏡看了很久,又做了聽力檢查。螢幕上的曲線起伏,我盯著那些波峰波谷,彷彿它們能解釋什麼。
「從客觀檢查來看,」醫生放下報告,語氣平穩,「你的耳朵結構沒有異常。鼓膜癒合良好,聽力也在正常範圍。」
我等待著。
他轉向我,用一種混合了專業與委婉的語氣說:「耳鳴有時是心理因素引起的。壓力、睡眠不足、焦慮都可能觸發。你最近生活上有什麼變化嗎?」
「我沒有壓力,」我說,「至少在耳鳴出現之前沒有。」
醫生點點頭,那個點頭的弧度我後來回想過很多次——不是認同,是一種程式化的安撫。
「我建議你可以嘗試放鬆技巧,或者,」他停頓了一下,「考慮看看心理醫生。有時候我們的身體會用這種方式表達情緒。」
「但我確實聽到聲音,」我重複,「不是幻覺,是真實的聲音。」
「我知道你聽到,」醫生說,他的眼神越過我看向下一位病人的病歷,「耳鳴是真實的感知。只是它的成因不一定在耳朵裡。」
走出診間時,我手裡拿著一張轉診單,上面寫著「精神科」。候診區的人來人往,我站在那裡,忽然明白了什麼是「被醫學拋棄」。
不是被拒絕治療,而是被歸類到「無法治療」的那一欄。
那天下午,我去了醫學院圖書館。
我在PubMed、中文醫學期刊資料庫裡搜索「耳鳴」。起初是帶著求證的心態——我想證明醫生錯了。但讀得越多,那個「錯」的邊界就越模糊,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深層的寒冷。
我讀到:
「耳鳴的病因複雜,多與聽覺系統損傷、神經異常、代謝失調等相關,目前尚無根治方法。」
「多數患者報告症狀隨時間持續,部分患者隨年齡增長症狀加劇。」
「長期耳鳴可能導致睡眠障礙、焦慮、抑鬱及認知功能下降。」
我一行一行地讀,像是在讀自己的判決書。
然後我看到了那個段落:
「部分患者描述耳鳴聲隨時間發生質變,從單純高頻音轉變為複雜聲響,包括人聲、音樂或具結構性的聲音,此現象可能與大腦皮質代償機制有關。」
我關掉網頁。
圖書館的冷氣很強,我卻在出汗。不是現在,我想。現在的聲音雖然痛苦,但至少它還是「聲音」。但如果它變了呢?如果有一天,我開始聽到「別的東西」呢?
我現在二十二歲。
如果醫學文獻說的是真的——症狀可能隨年齡加劇,可能變質,可能導致一系列連鎖崩壞——那意味著什麼?
意味著我的人生不是從此帶著一個缺陷前進。
而是我正站在一條向下的斜坡上,坡度只會越來越陡。
而我還這麼年輕。年輕,在這種計算裡,不再意味著「還有時間」,而是意味著「刑期特別長」。
我去了一間寺廟。不是祈求奇蹟,而是需要某種解釋——任何解釋都好。
法師聽完我的描述,安靜片刻,說:「身體是業的顯現。有時候,疼痛或異常是過去的因果成熟,有時候是未來的警示。」
「所以這是懲罰?」我問。
「不是懲罰,」法師搖頭,「是提醒。提醒你有些事需要放下,或者有些路需要轉彎。」
我請了一本《心經》。夜晚,當耳鳴變得難以忍受時,我就開始唸誦。起初是低聲唸,後來發現大聲唸誦時,自己的聲音能稍微蓋過它。於是我越唸越大聲,直到室友敲牆提醒。
我也嘗試冥想。盤腿坐在床上,專注於呼吸,試圖讓意識超越身體的感知。但越安靜,耳鳴就越清晰。它變成了一面鏡子,映照出我所有的焦躁與不耐。
同時,我發展出一套聲音對抗系統:
睡前必聽Angra的金屬樂,激烈的吉他獨奏和雙踏大鼓能製造足夠的噪音掩蓋。或是莫文蔚的〈他不愛我〉,重複的旋律有某種催眠效果。巴哈的無伴奏大提琴也行,那種單音旋律線條像一條細繩,我可以試著沿著它爬離自己的身體。
我還下載了白噪音APP。雨聲、海浪、風扇運轉、咖啡廳背景音。每種聲音都有用——在當下。它們像一堵牆,暫時擋住了那尖嘯。
但總有關掉的那一刻。
總有清晨醒來,發現APP已經自動停止,而耳鳴還在的那一刻。
它永遠在那裡,像一個忠實的獄卒,提醒我:所有這些都是暫緩,不是釋放。
三、山頂的懸崖邊
三個月後,我騎車上了木柵那座山。
時間是晚上十一點。我沒有告訴任何人要去哪裡,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。只是身體需要移動,需要離開那個越來越像囚籠的宿舍。
山路的彎道在車燈下明明滅滅。耳鳴在安全帽裡迴盪,和引擎聲混在一起,幾乎像某種扭曲的音樂。
山頂的觀景台空無一人。我停好車,走到欄杆邊。台北的夜景在腳下鋪開,萬家燈火,像倒過來的星空。
我拿出手機,又讀了一遍下午存的醫學摘要。那些字句我幾乎能背了:
「無根治方法。」
「可能隨年齡加劇。」
「可能導致嚴重心理併發症。」
我把手機收回口袋,雙手搭在欄杆上。金屬的冰涼透過掌心傳來。
這幾個月,我試過了所有我能想到的方法。醫療給了我轉診單,宗教給了我解釋,音樂給了我暫時的掩護。但沒有一樣改變了根本的事實:這個聲音不會離開。
而我的生活正在以緩慢、幾乎不可察覺的方式崩解。
功課開始落後,因為我無法在安靜的環境下閱讀超過二十分鐘。和李信妤的對話越來越短,因為我總是分心,總是疲倦,總是預支著耐心去應付下一刻的噪音。我甚至開始避免和人群相處——在喧鬧的餐廳裡,我得用更大的噪音去對抗耳鳴,結束後總是頭痛欲裂。
我看著腳下的城市,腦子裡開始計算:
如果現在的聲音強度是X。
如果醫學說它「可能」隨年齡加劇,就算每年只增加百分之一——不,就算每十年增加百分之十。
到我三十歲,聲音會是1.1X。
四十歲,1.21X。
五十歲,1.33X。
這還是最保守的估計。如果惡化得更快呢?如果它不只是變大聲,還「變質」呢?像文獻裡說的,開始聽見人聲、聽見音樂、聽見不屬於這個世界的聲音?
那麼到六十歲時,我會是什麼樣子?
一個無法忍受安靜,也無法承受喧鬧的人。一個在聲音的牢籠裡活著,卻已經聽不見真正世界的活死人。
欄杆下的懸崖並不特別深,下面有樹,有緩坡。但我知道,從這裡跳下去,足夠了。
這個念頭出現時,沒有戲劇性的顫抖,沒有淚水。它冷靜得像在解一道數學題:
已知:痛苦會隨時間加劇。
已知:目前無解。
求:最小化總痛苦的方式。
解:如果總痛苦 = ∫(痛苦強度) dt,從現在積分到死亡,那麼提前結束積分區間,似乎能減少總量。
我放開了一隻手。
不是因為衝動,是因為計算完了。
就在這時,手機響了。
螢幕上顯示「哥哥」。我盯著那兩個字看了三秒,才接起來。
「喂。」
「你在哪?」他的聲音背景有車聲,應該還在加班。
「山上。」
「這麼晚?」他停頓,「一個人?」
「嗯。」
電話那頭沉默了。我能聽見他敲鍵盤的聲音,一下,兩下。然後他說:
「我上去。」
「什麼?」
「我說,我上去。高雄到台北,現在開車,天亮前到。」
「不用——」
「要。」他打斷我,「你就在那裡,不要動。等我。」
又是沉默。這次更長。
然後他說:「記得手術那天晚上嗎?我說,這不是你一個人的事。現在還是。」
電話掛斷了。
我握著手機,聽著裡面的忙音,然後是耳鳴。它們交織在一起,像某種荒誕的二重奏。
我沒有跳。
不是因為突然有了希望,不是因為被愛感動,不是因為任何勵志的理由。
只是因為,當有人說「我過來」的時候,你很難在那一刻轉身跳下去。
我沿著欄杆滑坐在地上,背靠著冰冷的水泥牆。山風很冷,我抱著膝蓋,看著台北的燈火一盞一盞熄滅。
天快亮時,我站起來,發動摩托車。
哥哥沒有真的來。天亮時他傳了訊息:「我到公司了。你還在山上嗎?」
我回:「下山了。」
他:「嗯。活下去。」
四、開始另一種生活
下山的路在晨光中顯露出來,和我昨晚上來時是同一條,卻看起來完全不同。
我騎得很慢,耳鳴在清晨的安靜中格外清晰。但不知為何,我不再試圖對抗它了。我讓它存在,像讓風存在,讓引擎聲存在,讓這個世界存在。
回到宿舍時,天已濛濛亮。我輕手輕腳地開門,發現書桌上放著一個塑膠袋,裡面是溫熱的豆漿和飯糰。手機裡有一則李信妤不久前傳來的訊息:「看你昨晚沒回來,猜你可能又熬夜。請早起的同學順便帶了份早餐,放你桌上了。」
我回傳:「謝謝。」
盯著那簡單的兩個字,我站了一會兒,然後才拿起早餐。食物很暖,但那種溫暖抵達不了更深的地方。我走進浴室,讓熱水沖刷一夜的疲憊與露氣。
那天之後,我沒有停止尋找方法,但我改變了尋找的性質。
我不再尋找「治癒」,因為醫學已經告訴我,那扇門關上了。
我尋找的是「共存的方式」,但就連這個詞都太樂觀。更準確地說,我尋找的是「如何在監禁中活著」。
我開始記錄:什麼情況下耳鳴會稍緩?什麼情況下會加劇?什麼聲音能有效掩蓋?什麼時候該放棄抵抗?
我像一個獄卒研究囚犯,但囚犯是我自己。
有時候,在極度疲憊的時刻,那個山頂的計算會回來:如果終點已經確定,為什麼還要走這段路?
但我沒有答案。我只是繼續走。
因為哥哥那通電話,不是給了我活下去的理由,只是暫時移走了死去的選項。
而我發現,當「死亡」從選項中被移除後,人會發展出一種奇怪的韌性。不是勇敢,不是堅強,更像是一種惰性——既然不能結束,就只能繼續。
幾個月後,我畢業了。
收拾宿舍時,我找到那本《心經》,書頁邊緣已經被我捏得捲起。我把它放進紙箱,和其他不再需要的東西一起封存。
耳鳴還在。
我知道它會一直在。
醫學沒有告訴我它一定會變壞,但醫學也沒有任何證據能告訴我,它不會變壞。
所以我活在一個延遲的判決裡。刑期未定,但監禁是確定的。
我接受了這個。
不是接受痛苦,是接受「這就是我的身體,這就是我的現實」。
而這種接受,沒有任何解脫感。它只是一種認知的校準:從此以後,我要用一個囚徒的身份,活在自由的世界裡。
摩托車騎出校門時,陽光照在背上。
耳鳴在安全帽裡尖嘯,像永不停止的背景音樂。
我朝著第一個工作的方向前進,知道自己不會被治癒,知道自己可能在這聲音中逐漸老去,知道未來也許有更糟的變化在等待。
但此刻,我還活著。
活著,並且準備好,用這副帶著缺陷的身體,走進那個要求所有人健全的世界。
我知道這很難。
我知道這不公平。
但我已經計算過了——既然不能死,就只能活。
而活著,就意味著要找到一種方式,和這永恆的聲音,一起走向那個只會變得更吵的未來。
贊贊小屋小說作品集:
紅衣還願、大太陽奇遇記、未來列車、三年後的妻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