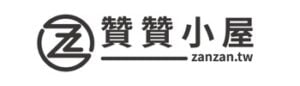(小說)三十年耳鳴3:你不動,但時間仍然在走
同學會上,我發現世界早已往前走,而我停在原地。與李信妤的重逢,讓我第一次明白,耳鳴不是命運,是我用來逃避人生的藉口。我終於被時間推開了。

一、同學會:世界已經往前走了
同學會選在台北東區一間居酒屋。包廂裡人聲鼎沸,燒烤的煙霧和啤酒泡沫一起蒸騰。這正是耳鳴理論上最不會出現的場合——各種頻率的聲音交織成厚厚的音牆,足以淹沒任何單調的內在噪音。事實上,整個晚上前半段,它真的不在。或者說,我沒有「聽見」它。我的注意力被喧鬧拉著走:阿傑在講他申請美國博士班的瘋狂計畫,小薇抱怨新創公司的加班地獄但眼睛發亮,家明計算著台北可怕的房價卻又帶著某種甜蜜的焦慮。
我聽著,點頭,偶爾插話。我的回應都在正確的時間點上,笑聲也合群。在這個由噪音構成的保護罩裡,我幾乎感覺自己是「正常」的。幾乎可以假裝,我和他們一樣,煩惱的是未來,而不是當下。
然後,聲音從包廂另一頭飄了過來。
是李信妤和幾個文學院朋友的對話。我沒有刻意聽,但話語自己鑽進耳朵。
「……所以你真的要搬去台中?」
「嗯,他工作在那邊。」李信妤的聲音平靜,清晰。
「哇,遠距離耶,沒問題嗎?」
「試試看啊。不行再想辦法。」
一陣笑聲。有人說:「你也太瀟灑了吧。」
就在那個瞬間——當「他」這個代名詞明確指向一個我不認識的、卻能讓她願意遷移的對象時——包廂裡的所有背景噪音,忽然像被調低了音量。
不是真的變安靜,而是我的感知濾網被瞬間切換。
然後,它出現了。
那熟悉的、高頻的嘶聲,像一根冰冷的細針,精準地刺穿了所有熱鬧的偽裝,直接抵達我的鼓膜內側。它一直都在嗎?還是我的大腦在我感到失落的那一刻,主動把它從背景裡「提拔」到了前臺?
我端起啤酒杯,喝了一大口。冰涼的液體滑過喉嚨,但胸口那塊下沉的感覺沒有被沖走。耳鳴聲穩穩地坐在聽覺的中心,彷彿在宣示:看吧,無論外面多麼喧囂,你內在的荒蕪永遠有一道專屬的配樂。
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:耳鳴從來不只是生理的聲音。它是一個開關,一盞警示燈。當我意識到自己與世界的連結正在斷裂,當我感到自己「被留下」時,它就會亮起,發出尖銳的鳴響。不是因為安靜,而是因為「我意識到自己沒在往前」,因為我內在的「靜止」與外界的「流動」產生了刺耳的摩擦。
聚會在十點左右解散。大家在店門口道別。李信妤走過來時,耳鳴正佔據著我大半的聽覺頻道,讓她的聲音聽起來有點遙遠。
「嗨,」她說,「好久不見。」
我抬起頭。「嗯,好久不見。」
「你最近好嗎?」
「……還好。」我說。在耳鳴的伴奏下,連說謊都顯得格外空洞。
她看了我兩秒,然後點點頭。「那,再聯絡。」
「好。」
她轉身離開。我站在原地,耳鳴聲隨著她的遠去似乎又清晰了一些。它不再只是一個症狀,而像一種即時的情緒聽診器,將我內心細微的塌陷轉譯成永不休止的頻率。
騎車回家的路上,我一直在想。 原來,最可怕的不是耳鳴在安靜時出現。而是即使在最吵鬧的人群中,只要心一沉,它就會準時赴約。
某些東西,已經永遠錯過了。 而提醒我這個事實的,不是記憶,不是畫面,是我自己大腦產生的、永恆的嘶聲。
二、回憶:他曾經不是現在這個人
那時候,我們會談論死亡。
不是具象的、充滿恐懼的死亡,而是作為哲學概念的死亡。大二那門「存在主義與現代人生」的通識課,教授是個頭髮花白的老先生,說話慢條斯理,但每句話都像在鑿石頭。
「海德格說,人是向死存在的。」他在台上說,「不是因為我們終將死亡,所以人生無意義。恰恰相反,正因為死亡是必然的,我們的存在才需要被認真對待。」
下課後,我和李信妤留在教室討論——不是因為特別好學,是因為那時候的我們,真的相信這些問題很重要。
「如果死亡是必然的,」我當時說,「那所有的計畫、所有的努力,不都是一種自我欺騙嗎?假裝那個終點不存在。」
李信妤想了一下。「也許正因為終點存在,過程才需要被認真對待。就像你知道電影總會結束,但你不會因此就快轉到結局。」
「但如果過程充滿痛苦呢?」我問,「如果活著本身就是一種折磨?」
她看著我,眼神裡有某種現在想來近乎天真的認真。「那就要問了:是活著本身痛苦,還是你對活著的想像讓你痛苦?」
那時候的失眠,和現在的失眠不一樣。
那時候的失眠,是腦袋停不下來。各種想法互相碰撞,關於自由意志,關於決定論,關於這個世界到底是一個巨大的機械,還是我們真的能選擇什麼。我會在深夜兩點傳訊息給李信妤:「你睡了嗎?」
通常五分鐘內她會回:「還沒。在想什麼?」
然後我們可以聊一個小時。透過宿舍的內線電話,壓低聲音,怕吵醒室友。聊到後來,話題會從哲學滑到生活,滑到某個老師奇怪的腔調,滑到學校後門新開的滷味店。
我記得很清楚:只有在那些對話裡,耳鳴會消失。
不是真的消失,是它退到了某個我意識不到的深處。不是因為愛情——那時候我們之間沒有愛情,只有一種智力上的親密——而是因為,在那種對話裡,我被完全拉回了「當下」。我的注意力不在自己身上,不在那個該死的身體感知上,而在我們共同建構的那個思想世界裡。
有一次,快到天亮時,她忽然說:「其實我挺喜歡這種時候的。」
「喜歡失眠?」
「不是喜歡失眠,是喜歡這種……好像整個世界都睡了,只剩下我們還醒著的感覺。很安靜,但又不是孤單的安靜。」
我當時沒有回答,因為不知道該說什麼。現在想來,那可能是最接近「健康」的時刻——兩個人,在深夜裡,分享一種不帶痛苦的清醒。
而現在的我,再也無法擁有那種清醒了。
現在的我,在深夜醒來時,只有耳鳴陪伴。它不需要我回應,不會和我對話,只會永恆地、單方面地宣示它的存在。
我意識到一件事:耳鳴沒有拿走我的全部。
但它成為了一個完美的藉口。一個讓我停止思考未來、停止規劃、停止冒險的藉口。我可以把所有停滯都歸咎於它,然後安心地待在原地,看著時間從身邊流過。
就像一個被判了緩刑的人,整天盯著刑期何時到來,卻忘了在等待期間,自己其實還是自由的。
只是這種自由,需要勇氣去使用。
而我,早就把那勇氣弄丟了。
三、單獨見面:判決的反轉
咖啡廳是我們以前常來的地方。靠窗的位置,下午陽光斜斜照進來。她點了一杯熱美式,我點了烏龍茶。
「所以,」她攪拌著咖啡,「你要離開台北了?」
我愣了一下。「誰說的?」
「阿傑說的。他說你好像要去新竹工作?」
「喔,對。」我這才想起來。「還不確定,只是有在談。」
「為什麼想離開台北?」
這個問題很自然,但我卡住了。耳鳴在此刻維持著一種低調的背景嗡鳴,像遠處的變電器,存在但尚可忽略。 真正的答案太長,也太難堪。
「想換個環境。」我最後說。
她點點頭,沒有追問。沉默了一會兒,她說:「你最近好嗎?真的。」
這是第二次有人問我這個問題。第一次在同學會,我可以說「老樣子」。但現在,在這個陽光很好的下午,那個答案顯得過於敷衍。
我感覺到耳鳴的頻率微微上揚,像某種預警。「不太好。」我說。
然後我說了。
不是戲劇性的坦白,沒有眼淚,沒有顫抖。只是平靜地、像在描述一個天氣現象那樣,說了耳鳴的事。說了它如何出現,如何持續,如何讓我開始害怕未來。說了那個計算——如果現在是X,十年後是1.1X,二十年後是1.33X。
當我開始描述「老去的樣子」時,耳鳴的聲量明顯爬升了。它不再只是背景,而是開始與我的話語競爭頻寬。我必須稍微提高音量,確保自己的聲音能蓋過它——或者說,蓋過我對它的感知。
「我覺得,」我最後說,耳鳴在此刻達到一個清晰的高峰,像在為這句話打上著重號,「我不太可能給別人幸福。連讓自己幸福都很難了。」
說完後,我等待著。等待安慰,等待鼓勵。
李信妤沉默了很久。
她沒有看我,而是看著窗外。有個學生騎腳踏車經過。
在這次沉默中,耳鳴沒有減弱,但它改變了性質。從尖銳的嘶聲,變成了一種更寬頻的、類似電視空白頻道的噪音。彷彿我的大腦在等待,將所有感知頻道清空,準備接收某個重要的輸入。
「我知道你有耳鳴。」她終於說。
我愣住了。
耳鳴瞬間收縮成一個極細的高點,然後——第一次,在坦白之後,它竟然減弱了。像一個終於被認出的鬼魂,暫時退到了陰影裡。
「大三那年,有一次你跟我說你失眠,我說可能是壓力。你說是耳朵的問題。我那時候沒多想,以為只是暫時的。」她轉回頭,眼神平靜,「後來看你一直很累,黑眼圈很重,我猜可能沒好。但我以為……你是一個堅強的男生。你會找到方法適應。」
這句話不是責怪。但它像一把鑰匙,打開了某個我長期鎖住的房間。
耳鳴回來了,但這次它帶著一種不同的質感:不是攻擊性的,更像一種共鳴的嗡嗡聲,隨著我的心率微微波動。
「我不是不堅強,」我說,聲音比預期中的乾澀,「我只是……」
「害怕。」她接下去。
我點頭。
就在我點頭的瞬間,耳鳴又強烈起來。彷彿「承認恐懼」這個動作,按下了某個放大開關。
她喝了一口咖啡,然後做了一件我完全沒預料到的事。
「我有家族遺傳的心臟病。」她說,語氣像在說明天可能會下雨。「我媽那邊的。我外婆四十歲走的,我阿姨四十五歲。我媽現在五十歲,每天吃藥,不能爬樓梯,不能情緒激動。」
我張開嘴,但發不出聲音。
耳鳴發生了奇異的變化。它沒有消失,但突然變得很「遙遠」。像從我腦內轉移到了房間的某個角落,變成了一種客觀的環境音。我的全部注意力,被她的話釘在了當下。
「還有氣喘。從小的。你記得我有一次期中考到一半被送去醫院嗎?就是那個。隨身要帶吸入劑,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作。」
她看著我,眼神裡有一種近乎殘酷的清澈。
「你的耳鳴,醫學告訴你『可能會隨年齡惡化』。那是一個可能性,在未來,也許十年後,也許二十年後。」
「我的心臟和肺,醫生告訴我的是:『任何一天都可能出問題』。不是未來,是今天,明天,下一秒。」
包廂裡的音樂正好換到一首慢歌。鋼琴的前奏輕輕流瀉。
在這一刻,我的耳鳴——完全停止了。
不是漸弱,不是被忽略,是真正的、絕對的安靜。 彷彿我的大腦終於理解到,它一直用來衡量自身痛苦的標尺,突然被放在了另一把更巨大的尺旁邊。那個讓我夜不能寐的聲音,在「任何一天都可能死」的現實面前,失去了發聲的資格。
安靜持續了大約三秒。然後,耳鳴回來了,但它現在聽起來完全不同——它變小了,變柔了,變成了一種普通的、幾乎可以被歸類為「環境白噪音」的聲音。
「你害怕的是未來,」她說,「我害怕的是今天來不來。」
那一瞬間,整個世界翻轉了。
我腦中那個關於「判刑」的想像——那個我以為只有我背負的、特殊的、殘酷的判決——突然顯得多麼……奢侈。我擁有的是一個延遲的判決,刑期未定。而她,活在一個沒有判決書的牢房裡,因為獄卒隨時可能走進來,不需要通知,不需要理由。
「所以你要搬去台中?」我聽見自己問,聲音陌生。我的耳鳴此刻是一種穩定的低鳴,不再干擾對話。
「對。因為他想去,因為我想試試。因為我不知道我還有多少個『可以試試』的時間。」她停頓,「我不是勇敢,我只是沒有選擇。停下來等死,和往前走然後可能死,我選後者。至少看起來比較像活著。」
我看著她。我從來不知道她背著這樣的東西活著。
「你為什麼……」我開始問,但不知道怎麼結束這個句子。
「為什麼不說?」她幫我說完,然後笑了,一個很淺、很疲倦的笑。「說什麼呢?『嗨,我有心臟病,所以你們要對我好一點』?還是『對不起,我不能太開心,因為可能會死』?」
她搖搖頭。「生病已經夠慘了,我不想連我的人生都變成疾病的註腳。」
服務生走過來幫我們加水。水壺傾斜,水流進玻璃杯的聲音清澈無比——我發現自己能清晰聽見每個水滴撞擊水面的細微聲響,而耳鳴退居到了一個非常次要的位置。
我忽然明白了:耳鳴的強弱,從來不只和環境安靜有關。它和「我認為自己有多悲慘」成正比。當有一個更巨大的現實擺在面前時,我的大腦自動調低了它的音量,因為認知資源必須被重新分配,去處理更緊急的資訊——比如,我之前的自憐是多麼可笑。
「我不是要說你應該怎樣,」李信妤最後說,語氣軟化了一些,「我只是想說……你看起來像是被判了死刑,在等執行。但你其實還站在法庭上,只是你自己以為判決已經下了。」
她拿起包包,站起來。
「我得走了,約了房東看台中的房子。」
我送她到咖啡廳門口。下午的陽光依然很好。
「保重。」她說。
「你也是。」
她走了幾步,又回頭。
「如果你去新竹,」她說,「記得活著。不是『忍受』的那種活著,是『去做點什麼』的那種。」
然後她轉身,走進陽光裡。
我站在咖啡廳門口,很久很久。
耳鳴還在。但它現在聽起來,就像咖啡機的餘響,就像遠處馬路的胎噪。它只是一種聲音,不再是詮釋我整個世界的濾鏡。
我第一次意識到:我錯過的可能不只是她。
我錯過的,是那個在知道真相之前,還願意相信未來、還願意往前走的自己。
而那個「真相」,從來不是耳鳴的醫學預後。那個「真相」是:我一直以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,直到發現有人帶著更重的鐐銬,卻走在了我前面。
耳鳴在這一刻給了我最後的啟示——它隨我的自憐而生,隨我的比較而弱。它不是我的命運,它只是我看待命運的方式所產生的回音。
四、離開:他被推向下一段人生
離校的手續在一個悶熱的下午辦完。學生證被註銷,宿舍清空。四年的大學生活,最後裝進三個紙箱,寄回高雄老家。隨身只帶一個行李箱,去新竹。
新竹那間貿易公司給了offer,職稱是業務助理。薪水普通,但提供園區附近的套房宿舍。面試時,主管問我為什麼想來新竹。
我說:「想離開台北。」
他笑了,說年輕人應該多闖闖。
我沒有解釋。解釋太複雜,而且沒必要。我沒說的是,我也需要離開「高雄」——那個在我敘事裡等於「療傷」和「停滯」的地方。我需要一個全新的、沒有任何過去影子的坐標。
打包最後的行李只花了一個下午。一些書,幾件衣服,日用品。那本《心經》還在箱子底層,我沒有拿出來。李信妤在去台中前傳了訊息:「一路順風。」
我回:「你也是。」
沒有再說什麼。有些對話,說完了就是說完了。再多就是重複,而重複會稀釋原本的力量。
離開台北那天是週一,早上七點的火車。我拖著行李走到校門口的公車站,等往車站的公車。清晨的校園很安靜,有幾個早起跑步的學生經過,腳步聲規律地響起又遠去。
耳鳴在清晨的安靜中特別清晰。我聽著它,忽然想到一個問題:如果現在這個聲音強度就是X,而我真的要活到六十歲,那麼這三十八年,我要怎麼過?
以前的答案會是:忍受,計算,等待惡化。
但現在,在和李信妤那場對話之後,那個答案顯得……笨拙。就像一個人整天盯著天花板,擔心它會不會塌下來,卻忘了自己其實可以走出這棟房子。
公車來了。我把行李搬上車,刷了卡,找個靠窗的位置坐下。
車子啟動,台北的街景開始後退。經過我們常去的那間咖啡廳,經過那間半夜還開著的滷味店,經過那個我和李信妤曾經站在那裡討論海德格的教室大樓。
我沒有特別感傷。感傷需要一種對過去的眷戀,而我對過去的感情很複雜——那是我還能想像未來的時代,但也是我開始失去未來的時代。
火車上,我坐在靠窗的位置,看著風景從城市變成田野,從灰色變成綠色。耳鳴一路陪伴,像一個忠實但不受歡迎的旅伴。
我沒有想通什麼。
沒有突然的覺悟,沒有釋懷,沒有「從此我要勇敢活下去」的決心。
我只是不能再待在原地了。
待在台北,每一天都會是昨日的重複:醒來,對抗聲音,工作,逃避安靜,睡著,然後再醒來。而在這個循環裡,我會持續看著別人前進,持續感覺自己落後,持續用耳鳴當藉口,解釋為什麼我停在這裡。
新竹至少是陌生的。陌生的街道,陌生的人,陌生的房間。在那裡,我的停滯不會有對照組,我的耳鳴不會有歷史。我可以只是「一個有耳鳴的人」,而不是「那個因為耳鳴而停在二十二歲的人」。
這不是選擇,是被推著走。
被時間推,被同儕推,被那個下午咖啡廳裡的對話推。被一種模糊的、連自己都無法完全承認的羞恥感推——當你發現,一個背著更重擔子的人,走得比你還遠的時候。
火車進入新竹站。我拖著行李下車,月台上人潮洶湧。空氣中有種不同的味道,混合著風、和一點工業區的氣息。
公司的宿舍在園區附近,一棟大樓裡的套房。房間很小,但乾淨,有一面窗對著另一棟大樓的灰色牆面。我把行李放下,坐在床邊。
耳鳴在響。
這裡很安靜,比台北的宿舍安靜很多。沒有室友的動靜,沒有走廊的腳步聲,只有空調低沉的運轉聲。
所以耳鳴變得更清晰了。它填滿了這個陌生房間的每一寸空氣,宣示主權:無論你去哪裡,我都會跟著你。
我躺下來,看著天花板。
我沒有感到希望。
但我感到一種奇怪的平靜。就像一個終於接受自己病情的病人,不再每天追問醫生「我會好嗎」,而是開始問「那麼,現在該怎麼活」。
而「現在該怎麼活」,是一個我很久沒有想過的問題。
手機震動了一下。是哥哥:「到了嗎?」
我回:「到了。新竹。」
他:「安頓好跟我說。有空回高雄。」
我:「好。」
窗外天色漸暗。遠處園區的燈火一盞盞亮起來,在玻璃上投出冷白的光暈。
我知道,在接下來的日子裡,我會一個人在這個房間醒來,一個人面對這個聲音,一個人吃飯,一個人工作,一個人入睡。
沒有任何理解我的人在我身邊。
沒有任何知道我背著什麼東西的人,可以給我一個眼神,一句「你還好嗎」。
我將完全地、徹底地,獨自面對這一切。
而正是這種徹底的孤獨,讓我隱約感覺到危險——當一個人渴求被理解到這種程度時,任何說「我懂你」的人,都會像沙漠中的水一樣致命。
無論那水,來自什麼樣的容器。
(第三集結束)
贊贊小屋小說作品集:
紅衣還願、大太陽奇遇記、未來列車、三年後的妻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