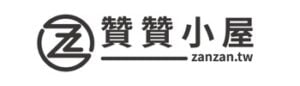(小說)大太陽奇遇記2:第二天,大白天不救人
走在回家路上。
今天的陽光又毒又猛,四十度高溫把空氣烤得發白。這種天不會讓人熱死,卻會讓人想死。我顧不得自己是男生,手一伸,把背包裡那把摺疊傘抽出來,啪一聲撐開,擋住頭頂那片殺人的亮白。

突然,一股燒焦味穿過滾滾熱浪,硬是鑽進我的鼻腔。
我下意識停住腳步,心臟漏跳一拍,四處張望——
走道乾乾淨淨,連片落葉都沒有。
旁邊那排樟樹挺得像衛兵,葉子在光裡綠得發亮。
沒有煙、沒有火、沒有垃圾燒起來的跡象。
但那股味道卻明顯變濃了,熱風一吹,直往臉上撲。
!!!
不對。
這個場景、這股味道——
我幾天前才遇過。
或者,是幾個月前?記憶像被人粗暴地洗過一遍,時間的順序斷成碎片,黏都黏不回來。但有一件事,我他媽的永遠忘不了:
那股燒焦味……是吸血鬼的臉正在融化。
那傢伙忘恩負義,我救了它,它回報我的是一張血盆大口,外加搶傘威脅,真是超級划算的交易。
那天逃回家,我立刻衝去巷口的全家,補買了一把新傘。藍色的。
從此,黑色傘?永遠拒絕。看到黑色就心裡發毛。
因為每次看到黑色傘面,腦子裡就會自動重播那兩排噁心、尖長、閃著詭異光的獠牙,排排坐好,對著我的手腕。
我同時還對自己發了毒誓:老子再也不走這條路回家。
而且我真的沒走過。
真的!我發誓!
……那我現在是在哪?神經接錯線了嗎?
我明明、確實、又他媽的回到了這條路上。
我整個人愣在原地,腳底像被熱柏油黏住,心臟被一種無名的恐懼擠得發痛。眼角餘光忍不住往頭頂一瞥——
一把黑色的傘。傘面漆黑,像能把光都吸進去。
幹!怎麼會是黑的!
我呼吸一滯。
我明明沒再買過黑傘!後來買的是藍的、黃的,最後一次,我清清楚楚記得,是在台北車站地下街挑了一把綠色的!我肯定。我發誓絕對沒有黑傘。
那麼,這把傘,是我自己從背包裡拿出來的?
還是——它自己回來了?
那股燒焦味變得更近、更真實,像無形的鉤子,拉著我往前。
走道盡頭到了。
左轉。
我的腳步僵硬得像機器人,但身體還是不受控制地轉了過去。
大約五十公尺外,柏油路面上,果然躺著一個男子扭曲的身影。
老樣子:一身歐洲中古世紀的時裝大 cosplay,布料層層疊疊,跟這個快熔化的城市格格不入。
老樣子:是那個吸血鬼。
如果是他,他現在一定衰弱到不成人形,像一尊被夏天惡意遺忘在馬路中間的蠟像,正一點一滴地塌陷。
一個卑鄙但無比合理的念頭,突然像毒藤一樣從我心底瘋長出來:
趁他快融化的時候,把傘搶回來。
但這個念頭剛冒出來,我就低頭看向自己手中——
我手上握著的,就是這把該死的黑傘。
那我背包裡……?
我猛地拉開背包拉鍊,手忙腳亂地翻找:礦泉水、兩本皺巴巴的書、一頂白色帽子……
找到了!
綠色的傘,好好地折成兩截,躺在最底下。
這才是我在台北車站地下街買的寶貝,我記得很清楚。
那麼,現在我手裡這把彷彿有生命般的黑傘——
是他還我的?
還是……他什麼時候,放在我手上的?
一股冰冷的寒意,瞬間鑽進我的脊椎,比頭頂的烈日更讓我發抖。
遠方那團糊掉的人形水彩,開始蠕動了。
緩慢、掙扎,像電影裡貞子最後爬出電視機那一幕,充滿非人的詭異感。
我的雙腿當場就想後轉,用百米衝刺的速度逃離。但「見死不救」這四個字,像秤砣一樣吊在我的良心上,沉甸甸的。加上眼前這雷同到可怕的場景,強行在我腦子裡倒帶播放,我對這件事,竟然可恥地生出了一絲……好奇。
反正他現在半融化,軟趴趴一灘,暫時也咬不到我。
我決定靠近。
但這次,我絕不會再讓他碰到我的傘!任何一把都不行!
我屏住呼吸,沿著人行道最右側、貼著牆根的狹窄陰影,像忍者一樣偷偷前進,每一步都輕得沒有聲音。
靠近到足以看清的距離時,我倒抽一口涼氣。那根本不能算是一張臉。像一幅水彩畫被暴雨沖刷過,五官模糊成一團污漬,皮膚融成粉紅與焦黑交雜的肉泥,邊緣還在滋滋作響,冒出細微的煙。
燒焦味混雜著一種像融化塑膠的劇烈化學氣味,濃烈到令人作嘔。
如果……我就這樣放著不管,他真的會變成一灘什麼都不剩的肉醬嗎?
「Help……Help……」
那團糊爛的肉泥裡,竟然傳出了虛弱至極的英文求救聲,氣若游絲。
幹,他又快死了。
為什麼我命中注定要當這個吸血鬼的專屬急救員?這什麼鬼差事?
我深吸一口那令人反胃的空氣,試圖壓下狂跳的心臟。然後——我做了一個決定。我慢慢地、刻意地,把手中撐開的黑傘,收了回來。
金屬傘骨喀啦一聲閉合,將那片小小的庇護陰影徹底撤除。
嘿嘿。
一股混雜著恐懼與報復的快感湧上來。
也許這次,風水輪流轉,輪到我復仇了。
熾烈的陽光毫無阻擋地直射在我背上,燙得皮膚發疼。我慢慢轉過身,背對那團正在溶解的生命,一邊邁開腳步,一邊在心裡笑著對自己宣告:
這次,我要——
見、死、不、救。
我握緊收攏的黑傘,把它當作一根勝利的權杖,昂首闊步走向前方的路口。大太陽將我的背影拉得長長的,彷彿在無聲宣告著「我終於反抗成功」的虛幻自由。
然而,就在我一轉彎,以為能將那噁心的景象和氣味拋在身後的瞬間——
一股比先前濃烈十倍、像是直接焚燒廢鐵橡膠的刺鼻氣味,猛地竄了上來,兇狠地衝進我的鼻腔,嗆得我眼睛發酸,幾乎流淚。
直覺像警報一樣在腦中尖嘯:
不對!有鬼!
我猛地轉回頭,望向剛才的位置——
遠遠地,柏油路面上,原本還勉強有個扭曲人形的地方。
現在,只剩下一灘濃稠、死寂的黑色液體。
那黑水在毒辣的陽光下持續「滋滋」作響,瘋狂冒著白煙,像熱油鍋裡被滴進了水,激烈地反應、沸騰、蒸發。
我心裡某個地方,像是突然被一隻冰冷的手狠狠揪了一下,悶痛驟然炸開。
靠邀……我真的……見死不救了。
一種原始的、幾乎是本能的內疚感,來得比任何理性思考都要更快、更兇猛。我腦子還沒想清楚,身體已經先動了——我抓緊那把我以為屬於我的黑傘,像被什麼無形的線牽引著,轉身朝那灘恐怖的黑水走回去。
腳步越靠近,那股混合焦臭與腐敗的氣味就越濃烈,黏膩地糊在喉嚨口,像鞋底踩到了高溫融化的塑膠,每一步都扯著噁心的絲。
我站定在那灘仍在微微滾動的黑水旁。陽光直射,曬得我頭皮發麻。幾乎是無意識地,我啪一聲撐開了手中的黑傘。
傘面張開,一片不規則的、窄窄的陰影,落在我腳邊,也覆蓋了部分冒煙的黑水。
就在那一瞬間——
驚人的事情發生了!那灘死寂的黑水活了過來!它像擁有意識的黑暗活物,猛地向傘影覆蓋的陰涼邊界收縮、退散、躲避陽光!滋滋的冒煙聲驟然加劇,黑水的表面開始劇烈翻騰、凝固、向上堆疊、重組!
先從那團凝聚的黑暗中最快浮現的,是一隻完整的人類手臂,五指張開,皮膚還帶著濕漉漉的黑亮光澤。
然後是肩膀、胸膛、脖子……
像倒放的毀滅影片,又像無形的積木手,將打散的血肉重新拼湊成人形。
我嚇得魂飛魄散,腿軟得幾乎站不住,轉身就想拔腿狂奔——
唰!
那隻剛凝聚成形、還半是液態半是固體的手,以快得看不清的速度,一把死死抓住了我的腳踝!
觸感冰涼、黏膩,卻蘊含著驚人的、無法掙脫的力量,像鐵鑄的捕獸夾!
「你真的……走了?」
那聲音直接從他那正在修復的破碎喉嚨裡擠出來,嘶啞乾裂,像被陽光徹底烤裂的氣音,卻充滿了某種令人膽寒的質問。
他的臉尚未完全恢復,半邊顴骨還暴露在空氣中,閃著詭異的光澤,另外半邊勉強撐起的皮肉,顫抖著睜開了一隻眼睛。
那隻眼睛死死地
盯著我
質問我
審判我。
我腦子裡一片慘白,只剩下求生本能驅動著嘴巴胡亂開合:
「不不不!我剛剛只是……嗯……去確認路口方向有沒有危險!然後我覺得……既然你把黑傘『還』給我了……我、我這不是回來救你了嗎!」
他的獠牙,就在我眼前,從牙齦中緩緩地、威脅性地生長回來,閃著白玉般卻冰冷的光澤。語氣也迅速恢復了那種記憶中欠揍的、貴族式的高傲與慵懶:
「你知道我需要什麼。」不再是請求,而是冰冷的陳述。
我幾乎是彈跳般地動作起來,立刻將黑傘高高撐好,手臂發抖卻精準地傾斜傘面,讓那片救命的陰影完整地、嚴絲合縫地籠罩住他正在重組的身軀。
灼燒的「滋滋」聲停止了。
刺鼻的白煙迅速散去。
他就像按下快轉鍵的影片,肉眼可見地從一團混沌重新凝聚、塑形,恢復成那個穿著古怪、面容蒼白英俊的外國男子模樣。
我的理智在尖叫:完了完了完了!又來了!歷史重演!
我的身體卻無比誠實:乖乖地、小心翼翼地伸手扶住他(觸手一片冰涼),像個盡職的僕從,攙著他往不遠處那個該死的、熟悉的涼亭走去。
到了涼亭的陰影裡,他幾乎恢復了八成的體面,甚至還有餘裕用纖長蒼白的手指,慢條斯理地整理了一下襯衫的領子與外套的皺褶。那副從容的「優雅」,與幾分鐘前柏油路上那灘沸騰的黑水,簡直判若兩人。
然後,他朝著我,平靜地伸出手,掌心向上:
「傘。」
我咽了口根本不存在的唾沫,雙手將那把漆黑、沉重、彷彿帶著不祥溫度的傘遞了過去,臉上擠出一個比哭還難看的、勉強稱之為「笑」的表情:
「那個……我書包裡還有綠色的傘,我、我不需要這把黑的了,就…留給你吧。真的,不用客氣。」
他接過傘,指尖無意間擦過我的皮膚,冰冷如屍。他沒有立刻打開,只是不疾不徐地說,聲音平緩卻帶著千斤重量:
「這把傘,從未屬於你。」
我全身的血液,在那一瞬間,彷彿真的徹底凍結,連指尖都感到刺骨的寒冷。
他這才輕輕撐開黑傘,坐在涼亭最深處、陰影最濃重的地方,讓黑暗完全包裹住他。那一瞬間,他彷彿褪去了所有人類的偽裝,回到了他真正所屬的位置:
夜的生物。
我悄悄往後退了幾步,腳跟碰到涼亭邊緣的台階,準備抓住機會,用最快的速度逃離這個夢魘。
他似乎察覺了我的意圖,緩緩抬起那雙已經恢復深邃碧藍的眼睛,目光像冰冷的蛛絲,纏繞過來:
「下次……」他頓了頓,嘴角勾起一個極淡、卻毫無溫度的弧度,「別再遲到。」
我整個人僵在原地,像被瞬間冰封。
我不敢問「什麼下次?」。
更不敢問「遲到是什麼意思?」。
我只知道,我必須立刻、馬上、現在就跑!
越快越好!越遠越好!
我轉身,用盡全身力氣拔腿狂奔,心臟在耳邊擂鼓,風聲呼呼刮過臉頰。
可是,在拚命奔跑的途中,在那幾乎要炸裂的恐懼與喘息間,我怎麼都擺脫不了一種詭異的、逐漸清晰的感覺:
剛才那一幕,不是我回去救了他。
更像是……
是這把詭異的黑傘,牽引著、甚至脅迫著我,回去完成它「主人」所需的儀式。
贊贊小屋小說作品集:
紅衣還願、大太陽奇遇記、未來列車、三年後的妻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