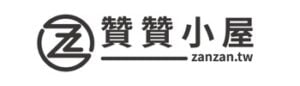(小說)紅衣還願2:已被擦去姓名的借據與利息
孩子失蹤後的第八天,林秀月回到廟裡查證十二年前的發財金借據。名字被抹去、記憶開始崩裂,她逐漸明白,小瀚並非偶然消失,而是早被標記的利息。

第一幕|名字的重量
晨光透過廚房紗窗,在餐桌表面切出細密的格狀影子。
林秀月坐在其中一格光裡。那張泛白的借據攤在她面前,十二年前的墨跡在晨光下顯得格外清晰——陳文雄,三個字,孤零零地占據借款人欄位。沒有塗改,沒有遮蓋,彷彿從一開始就只該有這一個名字。
她沒有觸碰那張紙,只是看著。像在觀察一件陌生但註定要進入她生命的器物。
陳文雄走進廚房時,腳步很輕。他停在她身後兩步遠的地方,沒有靠近餐桌。林秀月聽見他的呼吸,淺而克制。
「你吃飯嗎?」她問,聲音平淡,像在問今天天氣。
陳文雄頓了一下。「……好。」
她起身,從電鍋裡舀出兩碗昨晚的剩粥,放上餐桌。一碗推到自己對面,一碗留在自己這側。筷子擺好,醬菜從冰箱取出。一切都進行得過分正常。
陳文雄坐下,端起碗。他的視線避開那張借據,但林秀月知道,他每一個動作都在感知那張紙的存在——它像一片薄刃,橫在他們之間的空氣裡。
沒有人提起它。
粥喝到一半,林秀月放下筷子。「我今天去廟裡一趟。」
「去做什麼?」他的聲音有點緊。
「看看十二年前的借據正本,」她說,語氣就像說要去超市買菜,「廟裡應該有存底。」
陳文雄的手指微微收緊,但沒有阻止。他只是問:「需要我陪你去嗎?」
「不用,」林秀月起身收碗,「你看家。萬一有電話。」
她說的是「萬一有電話」,不是「萬一有小瀚的消息」。這個細微的用詞轉換,兩人都注意到了,但誰都沒有點破。
北帝君代天府的香火依然鼎盛,年節的氣氛還沒完全褪去。林秀月穿過拜庭,直接走向廟務辦公室。一位中年志工正在整理金紙,抬頭看見她,認出了她——這幾天來找孩子的母親,廟裡的人都記得。
「陳太太,」志工放下手邊工作,「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?」
「我想查一下,」林秀月從皮包裡拿出自己的身份證,「十二年前,我和我先生來借發財金的記錄。借據正本應該還在吧?」
志工露出為難的神色。「這個……借據我們會保留,但一般是十年內的比較好找。十二年前的,可能要翻倉庫的舊檔案。」
「我可以等,」林秀月的聲音很平靜,卻有一種不容拒絕的力道,「麻煩你們找找看。日期是民國九十二年,大年初三。」
志工看了看她,最後點點頭。「好吧,我去後面的檔案室找找。您在這裡坐一下。」
林秀月在辦公室旁的木椅上坐下。牆上掛著北帝君的畫像,神像的眼睛垂視著下方,慈悲而遙遠。她想起十二年前跪在這裡擲筊時,心裡那份沉重的懇求——不要垮,只要度過難關就好。那時她以為最難的是錢,現在才知道,錢債還清了,還有別的債會找上門。
半小時後,志工捧著一本厚重的線裝冊子出來。冊子封面是深藍色的布面,邊角已磨損發白。
「找到了,」志工翻開冊子,手指順著年份索引往下滑,「民國九十二年……在這裡。」
林秀月起身走過去。
冊子攤開的那一頁,是毛筆謄寫的借貸記錄。字跡工整,一筆一劃:
日期:民國九十二年正月初三
借款人:陳文雄、林秀月
借款金額:陸佰元整
借款緣由:家計所急
還款期限:一年內
備註:第一次借款兩個名字都在。
林秀月的視線在「林秀月」三個字上停留了幾秒。那是她的名字,被端正地寫在這裡,與陳文雄並列。她抬頭看向志工:「借據正本呢?我可以看嗎?」
「正本和副本是釘在一起的,」志工解釋,「我們一般是留正本在廟裡,副本給借款人帶回去。」他翻到下一頁,那裡用透明夾層固定著兩張泛黃的紙——正是借據的正本與複寫副本。
林秀月湊近看。
正本上,兩個簽名清晰可見:右側是陳文雄力道剛硬的字跡,左側是她自己娟秀的簽名。墨色一致,紙張也沒有異樣。
但她的目光移到下方的副本。
副本的簽名欄,透過複寫紙印出的字跡較淡,但依然可辨——只有陳文雄的名字。
她的名字那裡,是一片空白。
「這……」志工也注意到了,他推了推眼鏡,湊近仔細看,「奇怪,副本怎麼會缺一個名字?」
「當時經辦的人是誰?」林秀月問。
「這我就不知道了,十二年前的事,」志工搖頭,「而且這種副本缺名的情況,我們還真沒注意過。通常我們只核對正本,副本就是給借款人帶回去做憑證的……」
他的話停在這裡,沒有說完。
林秀月明白了他的未盡之言:廟方沒有隱瞞,沒有解釋,只是「沒注意到」。因為在他們的流程裡,副本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正本上有兩個名字,神明記得,廟方記得,這就夠了。
但對帶走副本的那個人來說,那片空白,或許有別的意思。
「我可以拍個照嗎?」林秀月拿出手機。
「這個……原則上不行,」志工有些猶豫,「但您的情況特殊,就拍吧。請不要外流。」
林秀月對著正本和副本各拍了一張照片。鏡頭對焦時,她注意到副本空白處的紙質——那裡似乎比周圍的紙張稍微光滑一些,像是被什麼東西輕輕磨過。
她沒有多問,只是道了謝,轉身離開辦公室。
走出廟門時,陽光刺眼。她站在廟埕中央,看著手機裡那兩張照片——正本上的並列名字,副本上的孤單名字。
這不是修改。
這是擦拭。
第二幕|回憶開始碎裂
林秀月沒有立刻回家。
她在廟埕角落的石椅上坐下,重新翻開那本線裝冊子的照片。目光停留在「借款緣由」那四個字:家計所急。
她記得那個願望。不是「發財」,是「不要垮」。記得陳文雄在擲筊前反覆確認流程的樣子,記得自己當時還笑著說:「神明又不是銀行,六百塊能救急就不錯了。」
但她用力回想,卻發現自己不記得陳文雄當時的表情。
這很奇怪。
十二年的時間,其他細節都還鮮活——廟裡濃厚的香火氣味、她穿的那件黑色長裙下擺沾了香灰、還願時他們一起寫在紅紙條上的「感恩北帝君護佑家宅平安」、甚至那天回家的路上下了點小雨,兩人共撐一把傘。
但唯獨陳文雄在簽下借據那一刻的臉,是模糊的。像一張對焦失敗的照片,只剩下輪廓,沒有細節。
彷彿有什麼東西,把他的表情從她的記憶裡挖走了。
「秀月?」
聲音從側邊傳來。林秀月抬頭,看見阿惠姐站在幾步外,手裡提著一袋剛買的金紙。她的臉色有些複雜,像是猶豫該不該靠近。
「阿惠姐,」林秀月收起手機,「來拜拜?」
「嗯,」阿惠姐走近,在她旁邊坐下,「也來看看你。這幾天……有消息嗎?」
林秀月搖頭。
兩人沉默了一會兒。廟埕的人潮在他們周圍流動,笑語聲、擲筊聲、小販的叫賣聲,構成一片熱鬧的背景音,卻襯得她們之間的安靜更顯沉重。
「我剛才去看了十二年前的借據,」林秀月突然開口,聲音很輕,「正本上,兩個名字都在。」
阿惠姐沒有接話,只是看著前方香爐升起的煙。
「但是副本,只有他的名字。」
煙被風吹散,扭曲成不規則的形狀。
阿惠姐終於轉頭看她。「秀月,有件事,我放在心裡十二年了。」
林秀月的手指微微收緊。
「十二年前你們來借發財金那次,」阿惠姐的聲音壓得很低,幾乎要被周圍的喧囂淹沒,「陳文雄不是一個人來的。」
空氣突然變冷了。
「我記得那天,有個女人跟著他,」阿惠姐繼續說,眼睛不看林秀月,只看著自己交握的雙手,「穿著……一件紅色的外套。不是大紅,是暗紅色,像乾掉的血那種顏色。當時我還覺得奇怪,因為平常陳文雄都是自己來,或者跟你一起。那天特別。」
「你認識那個女人?」林秀月的聲音平得可怕。
「不認識,」阿惠姐搖頭,「我只是,有點印象她的……額頭。」她抬起手指,點了點自己的眉心。「這裡,有一道疤。不是很明顯,但仔細看會看到。豎著的,大概這麼長。」她在空中比劃了一個約兩公分的長度。
林秀月突然感到一陣暈眩。
不是因為信息本身,而是因為——她記得那道疤。
記憶像被撬開的箱蓋,一個畫面猛地湧現:某個午後,她從市場買菜回家,在公寓樓下看見一個女人正在和陳文雄說話。女人背對著她,但轉身離開時,側臉的額頭上,有一道淺色的豎疤。
當時林秀月問:「那是誰?」
陳文雄的回答是什麼?她用力回想,卻只聽見自己的聲音在問,沒有他的回答。那段對話的後半部分,是空的。
「你想起來了,對不對?」阿惠姐看著她的臉。
林秀月沒有承認,也沒有否認。她只是問:「那個女人,後來還有出現嗎?」
「我不確定,」阿惠姐說,「廟口每天人來人往,我不可能每個人都記得。但那次之後,我有幾次看見陳文雄一個人來拜拜,神情……很緊繃。像是在還什麼債。」
債。
這個字懸在空氣中。
林秀月站起身,膝蓋有些發軟。「謝謝你告訴我這些,阿惠姐。」
「秀月,」阿惠姐拉住她的手腕,力道很輕,但很堅定,「有些事情,知道了未必比較好。你現在還有小瀚要找,不要讓過去的事分散你的心力。」
「如果過去的事,」林秀月慢慢地說,「就是現在的事呢?」
阿惠姐鬆開了手。她的眼神裡有某種東西——不是同情,也不是擔憂,更像是一種瞭然。彷彿她早就知道會有這麼一天。
林秀月轉身離開廟埕。走了幾步,她回頭看,阿惠姐還坐在石椅上,背影在香火煙霧中顯得模糊,像是要融入廟宇的背景裡,成為另一個見證者。
第三幕|選擇的分岔
林秀月站在廟埕邊緣,看著往來的人潮。
她有三個選擇。
第一,直接回家,把阿惠姐的話甩在陳文雄面前,逼他解釋。這會立刻撕裂他們之間最後一層薄紙,但也許能立刻得到答案——如果陳文雄願意說真話。
第二,繼續追查廟裡的記錄。十二年前的那筆借款,有沒有其他相關的檔案?還願時的記錄呢?香油簿呢?那個紅衣女人會不會在別的資料裡留下痕跡?
第三,回頭找阿惠姐,問更多細節。那個女人的長相、年紀、說話的口音、當時和陳文雄互動的樣子……但這也意味著要把阿惠姐更深地捲進來,讓一個外人知道他們的家庭正在碎裂。
她站在原地想了十分鐘。
然後轉身,重新走回廟務辦公室。
志工看見她又回來,有些驚訝。「陳太太,還有什麼事嗎?」
「我想看一下,」林秀月的聲音很穩,「十二年前我們來還願時的記錄。還有當年的香油功德簿,如果可以的話。」
志工這次猶豫更久。「陳太太,這些都是廟裡的內部文件,原則上不公開給香客查閱的。剛才讓您看借據記錄,已經是破例了……」
「我兒子失蹤第八天了,」林秀月看著他的眼睛,「警方還沒有找到任何線索。現在任何一點過去的線索,都可能幫助找到他。拜託你。」
她的語氣裡沒有哀求,只有陳述。但正是這種平靜,讓志工無法拒絕。
「……好吧,」他嘆了口氣,「但只能在這邊看,不能拍照。」
「謝謝。」
志工再次進入後面的檔案室。這次他去了更久,出來時抱著三本冊子:一本是還願記錄,一本是香油功德簿,還有一本看起來是活動簽到簿。
「民國九十二年你們來還願,是當年的年底,」志工翻開還願記錄冊,「這裡:十二月十五日,陳文雄、林秀月,還款陸佰元,加添香油貳佰元。」
記錄很簡潔,沒有特別之處。
林秀月接過香油功德簿。這本冊子更厚,頁面密密麻麻寫著捐款人的名字、金額、日期。她從九十二年一月開始翻,一頁一頁,手指順著名字往下滑。
大部分是熟悉的本地姓氏,金額從幾十元到幾千元不等。她翻到十二月,找到十五日那頁——他們還願的日子。上面確實有「陳文雄、林秀月,捌佰元」的記錄。
但她的目光被下面一行小字吸引。
那行字寫在他們記錄的下方,筆跡潦草,墨色較淡:
代 XX 還願 參佰元「這個『代 XX 還願』是什麼意思?」林秀月指著那行字問。
志工湊近看,皺起眉頭。「這……應該是代別人還願的意思。但這兩個字寫得太草了,看不清楚是誰。」
林秀月盯著那兩個被簡化成幾乎是符號的字。第一個字像是「王」,又像是「玉」。第二個字更模糊,像「芳」,又像「芬」。
「這種代還願的情況常見嗎?」
「不算常見,但偶爾會有,」志工說,「有時候是家人幫忙還,有時候是朋友。但一般會寫全名,寫這麼草的倒是少見。」
「能查出來是誰經手登記的嗎?」
志工搖頭。「十二年過去了,當時的志工現在大多不在這裡服務了。而且這種小額捐款,通常不會特別核對身份。」
林秀月沒有再問。她繼續翻看功德簿,尋找其他可能有「紅衣女人」痕跡的記錄。但直到翻完九十二年整年的頁面,都沒有再看到類似的「代還願」記錄,也沒有看到任何捐款人名字旁註記「額頭有疤」之類的說明——當然不會有,這只是她的妄想。
她合上冊子,遞還給志工。「謝謝你。」
「不客氣,」志工接過冊子,猶豫了一下,「陳太太,有句話我不知道該不該說……」
「請說。」
「廟裡有時候會有一些……特殊的案例,」志工斟酌著用詞,「有些人來借發財金,不是為了自己,是為了『抵債』。不是金錢的債,是別的債。這種情況,還願的方式也會不一樣。」
「什麼意思?」
「就是,」志工壓低聲音,「他們還的不是錢,是別的東西。而那個『別的東西』,有時候會由別人來代收。」
林秀月感覺背脊一陣發涼。「代收?誰來代收?」
「這我就不清楚了,」志工迅速搖頭,像是後悔說了太多,「我只是聽老一輩的志工提過。您就當我沒說吧。」
他抱著冊子匆匆走回檔案室,關上門。
林秀月站在空蕩的辦公室裡,突然覺得廟宇的寧靜不再令人安心,反而像一種漫長的等待——等待某個早就約定好的事物,在期限到來時現身。
她走出廟門時,看見阿惠姐還在金紙攤位前,正在整理一疊壽金。
林秀月走過去,站在攤位前,假裝挑選金紙。她拿起一疊刈金,用隨意的語氣問:「阿惠姐,你記得那個紅衣女人,長得怎麼樣嗎?大概幾歲?」
阿惠姐手上的動作停了一瞬。「年紀……當時大概三十出頭吧。比我年輕,但比你大一點。長相普通,就是一般人,除了那道疤,沒有特別讓人記住的特徵。」
「她說話有口音嗎?」
「沒有,就是本地口音,」阿惠姐說,「啊,對了,她左手手腕上,好像有個刺青。很小的,像個字,但我沒看清楚是什麼。」
刺青。
又一個細節。
「她後來還會來廟裡嗎?」
阿惠姐這次沉默了很久。最後她說:「秀月,有些問題,你應該問該問的人。問我,我給你的也只是碎片,拼不出完整的圖。」
「但如果連碎片都沒有,」林秀月輕輕地說,「我要怎麼知道該問誰?」
阿惠姐看著她,眼神裡有種深沉的疲憊。「去找你丈夫談吧。現在就去。趁還來得及。」
「來得及什麼?」
阿惠姐沒有回答。她轉身整理金紙,背影寫滿了拒絕。
林秀月知道,從阿惠姐這裡,她已經得不到更多了。
第四幕|爆點的形成
林秀月回到家時,已是傍晚。
廚房亮著燈。她走進去,看見陳文雄站在流理臺前,正在洗米煮飯。他的動作很慢,很仔細,像是在進行某種儀式。
她放下皮包,走到他旁邊,從冰箱拿出青菜,開始清洗。兩人肩並肩站著,各自忙碌,就像過去十二年的每一個尋常傍晚。
水聲嘩嘩。
「你去廟裡了,」陳文雄突然說。不是問句。
「是,」林秀月將青菜瀝乾,「我去看了十二年前的借據正本。」
陳文雄關上水龍頭。廚房裡只剩下抽油煙機的低鳴。
「還看了功德簿,」林秀月繼續說,聲音平靜得像在報告菜價,「看到一筆代還願的記錄,三百元,日期是我們還願的那天。名字寫得很草,看不清楚。」
陳文雄的手按在流理臺邊緣,指節發白。
「阿惠姐告訴我,十二年前我們去借發財金那天,有個紅衣女人跟你一起來。額頭有疤,左手手腕有刺青。」林秀月轉頭看他,「她是誰?」
沉默像實體一樣膨脹,填滿廚房的每個角落。
陳文雄緩緩轉身,面對她。他的臉上沒有林秀月預期的防禦、辯解,或憤怒。只有一種深沉的疲憊,一種被某種重擔壓了十二年、終於快要支撐不住的疲憊。
「借據上,」他開口,聲音沙啞,「本來是兩個人。正本兩個,副本也是兩個。」
林秀月等待。
「後來,」他深吸一口氣,「其中一個人……回來要求把她的名字去掉。從副本上去掉。」
「為什麼?」
「因為她說,如果她的名字和你的名字並列在那張借據上,願力就會分散,」陳文雄的眼睛看著地板,「她說,這筆債必須清清楚楚,誰借的,誰還,不能混在一起。」
「什麼債?」林秀月的聲音開始發顫。
陳文雄抬起頭,眼神直接而絕望。「秀月,我不能告訴你她是誰。因為她說,如果我說出來,她就會把小瀚帶走。」
林秀月手中的菜刀「噹」一聲掉在流理臺上。
「那時候小瀚還沒出生,」陳文雄繼續說,每個字都像從喉嚨深處擠出來,「我們甚至還不知道性別。但她說……她已經決定了,如果有機會,她會來要。」
「要什麼?」林秀月的聲音輕得像耳語。
「要一個孩子,」陳文雄閉上眼睛,「一個在『借據效力』期間出生的孩子。她說那是利息,是願力達成必須付出的代價。」
林秀月感覺整個世界在旋轉。她扶住流理臺,指甲陷進木頭邊緣。
「你是說,」她一字一字地問,「小瀚的消失,是十二年前就約定好的?」
「不是約定,是……條件,」陳文雄睜開眼,眼眶發紅,「我當時以為她只是說說,以為那只是一種迷信的說法。我以為只要我們把錢還清,就沒事了。但我錯了。還願那天,她又出現了。她說:『債還了,但利息還沒收。等時候到了,我會來取。』」
「你為什麼不告訴我?」林秀月的聲音終於裂開,露出底下的憤怒與痛苦,「十二年!你瞞了我十二年!」
「因為她說,如果我告訴你,利息會加倍,」陳文雄的聲音也在顫抖,「她說會帶走兩個。如果我們有第二個孩子,她也會帶走。所以我不能說……我甚至不敢讓你再懷孕……」
林秀月想起那些年,陳文雄總是小心翼翼做避孕措施的樣子。她曾以為他只是擔心經濟,現在才知道,那是恐懼。
「她是誰?」林秀月再次問,這次聲音冷得像冰。
「我真的不能說名字,」陳文雄搖頭,眼淚終於滑下來,「但我可以告訴你——你認識她。」
廚房陷入死寂。
抽油煙機不知何時停了。整個屋子安靜得能聽見自己的心跳聲,沉重而緩慢,像某種倒數。
林秀月看著丈夫哭泣的臉,看著這個同床共枕十二年、卻藏著如此巨大秘密的男人。她想起功德簿上那行潦草的「代 XX 還願」,想起阿惠姐描述的紅衣女人,想起自己記憶中那個額頭有疤的側臉。
然後她問出一個問題。
一個她其實已經知道答案,但必須問出口的問題。
「她有沒有來過我們家?」
陳文雄的哭聲戛然而止。
他沒有回答。
但他緩緩轉頭,看向客廳的方向。客廳牆上,掛著小瀚七歲生日的照片,孩子笑得眼睛彎成月牙,手裡拿著新買的玩具車。
陳文雄的目光在那張照片上停留。
三秒。
整整三秒。
然後他轉回頭,看著林秀月,什麼都沒說。
但那三秒的眼神,已經說出了一切。
【第二集 完】
贊贊小屋小說作品集:
紅衣還願、大太陽奇遇記、未來列車、三年後的妻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