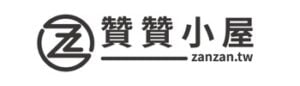毛蟲

那是一隻鮮豔讓人不敢觸摸的毛蟲,一看便覺得有毒。
是在爬山步道看到這隻毛蟲。他喜歡禮拜天早上去爬山,對他而言,這是一個星期中,最輕鬆自在的時光。
正當他享受只有一個人的爬山步道,突然間,發現腳下有個小東西在動,差點他一腳踩在那個小東西上,這個是什麼?他蹲下去看。
全身長滿透明刺毛如刺蝟一般的毛蟲。它身上一塊一塊不同顏色的鮮豔皮膚,不像是動物的皮膚,更像是西洋油彩畫裡的油彩,一塊一塊塗上去的。
那隻毛蟲有數不清的很短的腳,不停地前後擺動,它相對龐大的肉身,以如此蠕動姿態,從爬山步道的石子路,移動到路邊山林泥土地上。
這毛蟲知道我在看它嗎?怎麼好像躲進山裡面去的樣子?
正這麼想,那只隻毛蟲爬上路邊泥土崖了,幾乎是以垂直角度在樹根盤聚的泥土崖,百足之蟲往上爬。
毛蟲也在爬山呢!他突然感到親切,這裡沒有其他人,毛蟲成為他爬山的唯一同伴。
眼看著那隻毛蟲,就要爬到再也碰不到的距離,突然有一個奇怪念頭,他不想讓毛蟲逃走,趕緊隨手抓了根枯樹枝,拿出背包裡剛喝完的礦泉水空瓶,先引誘那隻毛蟲爬上枝樹枝,再由枯樹枝爬進瓶子裡。
用小刀把寶特瓶割幾個細長孔,好讓寶特瓶透氣,接著鎖緊瓶蓋,拿個塑膠袋包好寶特瓶,他再看了寶特瓶裡的毛蟲一眼,將瓶子放進背包。
帶回家吧。他住的公寓頂樓有幾個小盆栽,弄起來是個小花園,他打算把寶特瓶裡的毛蟲,放到自己花園裡。
回到租屋,從背包拿出瓶子,發現那隻毛蟲蜷曲成一團,一動也不動。
死了?他不敢相信,從爬山地方坐公車回家,也不過兩三個小時,雖然公車上他沒將瓶子拿出來,人很多,怕會嚇到別的乘客。
但他還特地在瓶子上,割幾條細長透氣孔,背包拉鏈也刻意留了間隙,沒道理會悶窒而死?
無論如何,毛蟲終究是一動也不動,好像是死了,但身上皮膚色彩仍然很鮮艷。他把瓶子帶到頂樓,將毛蟲倒在其中一個盆栽上,毛蟲千百隻腳,還是一動也不動,他挖一個土洞,將那隻毛蟲埋了。
當作沒有這件事發生。他有點後悔,當初不知怎地,把這隻七彩毛蟲裝進寶特瓶帶回家,可是再怎麼想,也沒有用,頂樓空氣突然變得很沈悶,他下樓,回自己房間。
一夜無語。
睡中無夢。
隔天早上,他到頂樓澆水,第一個想到的,是昨天埋葬毛蟲的那個盆栽,當他抬起澆水桶,要朝下灑的時候,愕然發現上面有一隻毛蟲,跟昨天那一隻,長的一模一樣。他後跳一步,吐了一口氣,向前察看昨天埋掉毛蟲的地方,挖了一陣,挖不出毛蟲屍體。奇怪的是,不久,每個盆栽都活生生的爬著一隻毛蟲。
同樣斑爛色彩的毛蟲。
看著這些盆栽上的毛蟲,他感覺如同颱風將至的沉悶,空氣很重,悶窒似的喘不過氣來。這些盆栽,他種幾個月了,很確定在頂樓的這些小植物,不會自己生出毛蟲來。
那天,一整天在公司他心神不寧,下班回家,他繞了點路,在路上找到店家,買了一瓶殺蟲劑。
這件事必須有個了結,他心中暗自決定。
回到家,爬到頂樓,他走到盆栽前面,睃巡了一遍又一遍,郤連一隻毛蟲也看不到。他沉默思索了一會兒,然後很仔細地再掃過一遍,又一遍,就是沒有色彩鮮艷的毛蟲踪影。
一隻都沒有。
早上明明看到很多隻的。本來,他帶著殺蟲劑來到頂樓,心跳很厲害,他根本不能確定,自己是否有膽量將殺蟲劑對準一隻隻的毛蟲,狂噴至死方休。
也許早上是幻覺吧,昨晚可能睡得不好,他放心鬆了一口氣,殺蟲劑留在頂樓,一個階梯一個階梯,慢慢地、踏實地,走回房間。
隔天早上,他剛醒來,莫名其妙感到很疲憊,意識不是很清楚,如同往常數不清的早晨,他第一個動作,是到浴室間刷牙洗臉。
「哇!」
剛走到洗臉台,還沒扭開水龍頭,往洗臉台一靠近,迷濛中睜開雙眼,赫然看到洗臉台裡,爬滿色彩鮮艷的毛蟲,一個個不停的蠕動,找空隙鑽,數不清的毛蟲腳在鑽疊蠕爬,整個洗臉台,看起來如同3D電腦的幾何圖形演示,炫目刺眼。
他本能反應的往後猛然一躍,撞到牆壁,昏迷過去。
發佈日期:2015-11-27
畫壼(1):因果

西方宗教大多是一神信仰,就是這個世界上帝存在,而且上帝只能有一個!
很難想像“只有”兩個阿拉同時存在的宗教,有的話,兩個阿拉打起來怎麼辦?就算阿拉不打起來,常常為宗教而戰的人類,也很容易為了各自的阿拉打起來!
為了避免兩個阿拉的困境,西方宗教大多是一神信仰:只有一個上帝存在。這樣的宗教,通常會把上帝當作是一切的根本、最終的解釋。例如說:你家小狗今天在路邊撒泡尿,是神的旨意,明天你家小狗在路邊咬人一口,也是神說了算。
很奇怪吧!如果繼續討論下去,就必須面對諸如自由意志呀、惡呀這一類的學術渣,麻煩到腦袋抽筋!
所以我比較喜歡東方宗教。
也就是佛教。
還記得,大學時中國哲學史的課堂上有一句話,怪里怪氣的教授說了一句怪話:“佛教是無神論者!”
哲學系畢業之後,很多東西我都還給怪里怪氣的教授了,現在盤點下來,大概只有這句話我還留著。
一直以來我搞不懂:明明釋迦摩尼、觀世音每天在身邊出没,為啥那個怪里怪氣的教授會說佛教無神?
現在,就在我打算說這個故事之前,假裝還是哲學系學生的我,仔細分析比較了西方基督教和東方佛教,突然我眼前一道閃光,有重大發現!
基督教信仰一個絶對的神,宇宙間所有的一切皆是神所賜。
佛教沒有絶對的神,更釋迦摩尼佛地說,每個人都不是神,可是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神。只要潛心修研佛法,悟得正道,人人都能夠成為佛教神。
釋迦摩尼、觀世音,在還沒有得道成佛之前,說他們是凡夫俗子,沒有人反對吧!
不同神學觀,帶來不同的因果觀。
基督教裡上帝是唯一神,所有一切都是上帝創造上帝決定,總之就是上帝說了算,衍伸到極端就是宿命論,很灰暗很悲劇色彩的。
佛教不一樣了!在佛教世界裡,每個人都有向上發展的潛力,萬宗萬法互為因果,所以因果關係變得瑰麗多彩。每個人被因果緊緊咬住,然而在此同時,每個人又有自行衍生因果的力量。
要我說的話,佛教信仰的唯一神就是因果。因果這兩個字,是佛教最吸引我的地方。
基督教徒不敢做壞事,是怕違背上帝旨意,死後下地獄,佛教徒不敢做壞事,是怕因緣果報,就算死後僥倖剛好地獄額滿了進不去,也會在下一次投胎轉世時,報應。
但,下輩子太遠啦,大壞蛋難保心存僥倖,想說下輩子投胎受苦關我屁事,於是壞事儘管照做,大鳴大放!
這時候佛法精深微妙的地方就來啦:善惡到頭終有報,不是不報,時候未到!除非你練就彌勒佛笑口常開的無敵境界,不然,誰沒有倒霉的時候?人生漫長,總有眼淚都快要掉下來的那一刻吧。
到了那個時候,夜深人靜,一個人回首前塵往事,不意外地發現:
自己當過壞蛋!!!
很多精彩的佛教故事,講了很久很久,其實要講的就兩個字:因果。
發佈日期:2015-10-16
圍巾(4)(完):沒有兇手的殺人案件
「原來……這就是你家。」酒店小姐一進門,緊緊抱住他。
儘管他明明知道老婆兒女都出國了,但是偷吃難免心虛,他張望四周神經兮兮的眼神,透露出他的緊張。
「緊張什麼,現在就只有我們倆。」酒店小姐依偎他懷裡撒嬌。
「說不定我老婆突然跑回來!上一次她本來說幾號幾號回來,結果提前幾天就看到她在家裡了。」他把她一整個抱起來,走進客廳再走進房間。
「如果真的這樣就更好玩了,大老婆小老婆都在,趙董你不是享齊人之福?」酒店小姐輕輕捏他一把。
他沒有答話。
那一瞬間,他想起十年起的自己,那時候的他還是個工廠工人,現在他能住像這樣的房子,能被酒店小姐稱之為趙董,原因只有一個:拜他老婆所賜。
酒店小姐小姐見他沈默不語,知道他心裡想著老婆,臉上閃過一絲不悅,但隨即轉化成笑臉,伸出手指撫摸他的胸膛。
她決定以最直接方式,打敗另外一個女人。
他感受到她身體溫暖,同時也享受她若有似無的輕撫,忍不住用力將她抱緊抱到床上,從她耳朵開始進攻。
他在外面偷情習慣了,這是第一次把女人帶進家裡,對他而言,有一種比打野味更新鮮的刺激感,對酒店小姐而言,在已婚男人的家裡上床,有一種完全征服的快感,不但是打敗眼前這個男人,更是打敗這個家裡的女主人。
他們在狂熱中達到高潮。

結束之後,她看到梳妝台上有個盒子,包裝精美,好奇問道:「那是什麼東西?」
「我老婆從老家帶回來的,一直沒拆,我問過她,她說要送人的,先放著。」他還沒從剛才的刺激中回復,這段話說的有氣無力。
「拿來我看看吧!」她一聽到是他老婆的東西,打定主意要搶過來。
「我老婆交待過的,先不要動它。」他察覺到她的想法,隱約覺得不太好。
「那我來幫你老婆檢查一下,看看這東西好不好!」她纏到他身上,伸手撫摸他的臉龐。
她知道,這個男人很老實,她知道這個男人要什麼,她可以完全滿足他,所以反過來,這個男人也要有點回應。
趙少海起身,顫抖著走到梳妝鏡,把那個盒子拿到床邊。
她接過那個盒子,滿足地打開,發現裡面是一條圍巾,顏色是很鮮艷的紅色。趙少海看著那紅色,鮮艷到不像一般的色料,簡直是浸泡過血一樣,有點可怕的鮮紅色。
「是真的!是那條圍巾殺了她!」他後來在法庭上說到這裡,臉上驚恐的表情讓人無法懷疑。「她把那條圍巾圍在脖子上,走到梳妝台照鏡子,沒想到那條圍巾忽然絞起來,狠狠勒住她的脖子,她想跟我求救,但根本發不出聲音。我見狀撲向前,可是無論我再怎麼用力,也無法把圍巾松開。
「我只能眼睜睜看著她倒下去,臉色發青腫脹,耳朵和鼻子流出血來,眼球明顯突出。慌亂之中我拿起剪刀,想直接把勒緊的圍巾連皮膚剪開,可是她雙手一直亂動,我沒辦法好好對準,等到我用腳壓住她的雙手,準備剪下去的時候,她已經不再掙扎,於是我探她口鼻,她死了……
根據測謊結果,他沒有說謊,可是沒人相信圍巾會自動把人勒死。依照案情關係人研判,唯一有殺人動機的是他老婆,可是他老婆回A國去了,有最佳的不在場證據。檢警想傳喚他老婆,可是他老婆一直留在A國,沒有回來,他案發後打過電話給老婆,想問那條圍巾的事,但老婆沒有接電話,後來是電話再也打不通。
他以過失殺人罪被起訴,但是實在找不到殺人的直接證據,案子拖了一年,到最後無罪釋放。案發之後他精神狀態不太好,再加上原本管理行政的老婆不在,工廠的營運一落千丈,到最後只得關掉。
他的房子車子和財產都還有,經濟狀況還可以,他也無心再開一次工廠東山再起,改行計程車司機,只求每天安穩度日。
他在A國的老婆兒女,沒有再回來過。
發佈日期:2015-10-12
圍巾(3):老婆與情人

結婚十年來,他第一次外遇。
在他飛黃騰達的這幾年,主動獻上青春肉體的女孩,一直都有,他沒接受過。他很清楚,有錢不怕沒女人抱,但他更清楚,他之所以有錢,都是因為他有個好老婆。
他的老婆,是A國人。A國是落後國家,工資水平低,最低薪資大概只有台灣的十分之一,所以很多人來這裡工作當外勞的,想賺點錢撈一筆回家。但是,也有少部份外勞家裡經濟狀況其實不錯,他們來這裡工作,只是純粹嚮往這裡的生活環境。
他的老婆就是屬於後者。他跟他老婆認識的時候,在同一個加工區上班,透過朋友介紹的。他想要一個女朋友,她想要一個B國男友,所以他們一拍即合,交往的速度很快,第一天在KTV認識就牽手,一個月內決定結婚。
婚前,他跟朋友借錢辦婚禮,婚後,他才知道老婆家裡經濟狀況不錯。娘家資助他一筆錢,讓他創業自己開工廠,他就跟他老婆兩個,他管業務生產,老婆管財務行政,短短幾年,把工廠做到現在規模。雖然不能跟上市的大公司比,但是和以前幫別人打工領死薪水來比,那肯定是差好幾萬光年的距離。
本來,他跟老婆感情好的沒話說,老婆也很爭氣,婚後不久就生個兒子。直到最近幾年,老婆生第二胞,才開始有點微妙的變化。
第二胞是女兒,在剛懷孕的時,老婆一直嚷著要帶這女兒回娘家,好不容易有個千金的他,當然不同意。他們為此爭執幾次,最後他脫口而出:你們A國是什麼地方?我怎麼可以讓寶貝女兒到那裡?聽到這句話的老婆臉色瞬間鐵青,她沒想到娘家資助他開工廠,她幫他打理工廠雜務,到最後,換來的是這樣一句話。
他們開始不太閒聊,他開始上酒店。
工廠的客戶總是要應酬,免不了花天酒地,以前這種場合,他都讓業務去,自己從不參加。有一次他晚上覺得煩,不太想回家,就跟業務一起去跑酒店應酬。
在那裡,他第一次見識到,B國成熟女人的撫媚,
他很快成為酒店一位紅牌小姐的恩客,每次去都是點她。他老婆每天都在公司,察覺到這件事,氣憤不過,帶著兒子女兒跑回A國去了。雖然一個星期後,回來了,但是帶著兒子女兒回娘家,有了第一次,之後,便成為一個常態。
在一次應酬中,酒店小姐得知他老婆兒女都不在家,緊緊纏住他:「帶我回你那個空虛的家,我來當你的老婆!」他雖然常跑酒店,但是帶小姐回家這件事,從來沒有想過,聽她這麼說,突然酒就醒了,睜大眼睛看著眼前這個女人,她嬌笑著說:「只是臨時的小老婆,一個晚上就好了嘛!」
他一想到回家之後的空蕩蕩,再想到老婆竟然把兒子女兒都帶回A國去,報復心理油然而成,便把她帶回家了。
發佈日期:2015-10-10
圍巾(2):老實的男人

關於人生際遇如何演變,地下街一整排的算命仙,誰也說不准。
特別是當你把時間的座標軸拉長。
一年半載的時間里,班上同學每個都差不多,公司同事也都差不多,可是如果把時間軸拉長到五年十年,那可不一樣,那是完全不同的故事。
坐在你隔壁的小胖同學,生活只有漫畫跟電動,畢業後幾年,女朋友交過好幾個,而且還分現任和候補!反過來看,你依然宅男加處男一枚。
每天跟你吃飯的小張,進公司才沒幾年,現在升到經理了,房子車子孩子一應俱全,反過來看,你依然是專員,只不過從一等專員升到資深專員,人生大事,還在緊鑼密鼓規劃中。
本來注定做工仔命的趙少海,十年前,還是工廠機械操作員,十年後,他自己開設一家工廠,雖然規模只能算微小型企業,但也夠他買別墅開賓士,頭銜聽起來如沐春風:董事長。
以前別人管叫他小趙,現在大家尊稱他趙董。
十年前的他,做夢都不會想到有一天,別人會尊稱他叫趙董,如同他沒想到有一天,婚外情小三這種全天下男人都會幹的好事,他也有一份。
他感覺自己膽子沒有這麼大過,他的心情,就跟國小第一次被同學慫恿爬牆到外面買飲料一樣,興奮、緊張、擔心都有,但是更多的是——血脈沸騰的刺激。當他拿出那件新買、色澤跟偷情一樣鮮艷的圍巾出來之際,他的手在抖,儘管他再怎麼屏氣凝神,手還是發抖,而他的聲音抖的更厲害:「這個…是…給你的…」
回答他的人,聲音嬌媚像顆糖一直在嘴裡,她的笑容男人無法拒絕,當她柔情似水依靠在他懷裡,他恨不得變成大猩猩把她緊緊抓住。
這麼一個妙齡女子的肉體,在他床上,任他進攻。
她嬌嗔,眼睛載著有顏色的隱型眼鏡,是艷麗的深藍色,水汪汪的特別吸引人、或者可以說,特別勾引人。她聽他聲音在顫抖,不禁微笑,她在床上玉體橫陳,卷抱著棉被頗有深意地看著他。
征服一個男人,這麼簡單,她數不清這是第幾個男人被她征服了。
他的手一直顫抖,拿在他手上那條鮮艷圍巾,也在空中顫動,從房間里大妝裝鏡看,兩個人都是靜止,只有他的手跟那條圍巾在顫動,色彩鮮艷讓人眼睛都看花了,有種說不出的窒息感。終於,她動了,起身伸出手來,卻不是去拿他手上的圍巾,而是去摸他的大腿,輕輕搔他大腿的癢,他觸電一般的驚嚇,分不清是害怕她的進攻、還是害怕搔癢,總之,他就是身體本能反應地往後縮。
這是她的必殺技之一,她知道這個男人完了,眼看就快要拜倒在她裙下,她噗哧一聲笑了出來:「害怕?後悔?」
「當然沒有!」他憤力為自己辯解,在這種情況下,很少有男人可以把持得住。
「抱我。」她直接下命令。
他鬆開手上的圍巾,真的變成一頭大猩猩,摟住她狂暴親吻與磨擦,這時的她彷彿一條水蛇,緊緊纏繞住他。
圍巾本來掉在床上,後來又被擠落到床腳邊的地上。
從小到大,他是個老實人,但是再怎麼老實的人,有錢有誘惑,還是會變成一個老實的男人。
發佈日期:
圍巾(1):一樁殺人事件

國小每天騎腳車回家,出校門後,繞學校左邊的馬路,那條馬路跟學校隔著圍牆,圍牆邊是一排松樹。那天吹著口哨,我如同往常,騎腳踏車經過學校旁小路,不經意望向那排松樹,有一個讓我觸目驚心的畫面,即使歲月如梭,到現在二十年後,那畫面還黏在我記憶里:
蒼白一張臉,彎彎的形狀跟月亮一樣,有眼睛鼻子嘴巴,只是沒有身體和脖子,就一張臉,孤伶伶掛在松樹上。
初看是月亮,再看是臉。
我嚇的狂奔回家。晚上剛好家人都不在,唯一讓自己驅妖避魔的方式,是玩任天堂紅白機,印象中是一款模擬1988年漢城奧運的遊戲,把聲音開到二樓都聽的到的程度,好像電動的聲音大了,自己的膽子也大了。哥哥擔心我,打電話回來,他聽到電動的聲音,知道我開得很大聲,頗有同感的覺得我應該沒什麼問題。
二十年後的話說回來,那掛在高高松樹上的,他媽的到底是臉還是月亮?那時候根本沒有仔細看,被嚇得一口咬定它就是,現在過了這麼久,再去回想這件事,開始它到底是月亮還是鬼臉。有些事就是這樣,剛開始發生一口咬定,等到時間夠久,人變得冷靜,十年後、二十年後,當初一口咬定的事到底真相如何,再也沒辦法摸著良心一口咬定。
長大之後我當律師,打過大大小小的刑事案件,每個案件都有被告,每個被告都有屬於他自己一口咬定的故事,通常十之八九,都是咬定自己清白無辜,最後案件結束,法官判下來,有罪無罪就只有這兩種結果,但是有些時候,判有罪,不能證明被告真的殺人放火,判無罪,也不代表被告真的清白無辜。
到底有罪還是無罪,就是我童年所看到松樹上的東西一樣,到底月亮還是鬼臉,時間衝刷過後,很可能再也分不清,更可能的是,再也不重要、再也沒有人關心了。
現在要講的故事,是一樁殺人事件,很多年之前發生的,當初我一口咬定,可是現在再回想起這個案件,我越想越覺得不對勁,所以我動筆把它寫下來,想借由寫作的過程,仔細再推敲一次事情的來龍去脈,希望能理出事情的真相。
殺人工具,是一條圍巾。
圍巾是很特別的服飾,尤其對於台灣而言,更是如此。淡水清晨六度的低溫,已經是打趴一整個冬天的最低溫了,這種氣候,圍巾變成是非生活必需品。於是,男生披圍巾,帥的有點像韓劇《冬季戀歌》里的斐勇俊,女生披圍巾,美的有點像韓劇《冬季戀歌》里的崔智友。於是,圍巾成為冬天里男女間送禮的最佳人氣小品,男生送女生圍巾、女生送男生圍巾,一點也不意外,沒有才是意外。
這是被告趙少海生平的第一條圍巾。
他一直是個老粗,台語話叫做工仔人的命,本來像他這類人,一輩子注定在工廠工地裡打滾,抽長壽煙、嚼檳榔、喝維士比,總是滿身大汗、總是臟兮兮,這些是一般對於藍領工人的刻版印象。
發佈日期:2015-10-0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