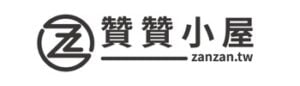(小說)紅衣還願5:以祝福斷開纏繞兩代的紅線
正月子夜,儀式啟動,林秀月在願力撕裂中直面契約真相。當母愛、執念與守護正面碰撞,她選擇以祝福改寫詛咒,斷開跨越兩代的債。紅衣還願,終於落幕。

第一幕|北斗燃燈
子夜零時,陳玉娟點燃了第一盞油燈。
燈火是幽藍色的,不是正常的橘黃。燈油散發出濃郁的、類似檀香混合藥草的氣味,在密閉的房間裡迅速瀰漫。林秀月坐在房間中央,身下是用石灰畫出的北斗七星圖案,她正對「天樞」星位。
陳玉娟穿著暗紅色的儀式服——那是一件式樣古舊的對襟長袍,邊緣繡著褪色的金線。她的頭髮完全披散下來,遮住半邊臉頰,露出的那隻眼睛在幽藍燈火映照下,顯得不似活人。
「北斗主死,亦能轉生,」她低聲吟誦,點燃第二盞燈,「七燈連星,通路自成。」
林秀月感到房間的空氣開始變質。不是溫度變化,而是一種密度上的改變——空氣變得黏稠,每一次呼吸都需要用力。她按照陳玉娟的要求,雙手平放在膝上,掌心向上,保持絕對靜止。
「契約承載者,上前,」陳玉娟說。
陳文雄站在牆角,臉色慘白。他被迫換上了一件白色的麻布長衫,看起來像喪服。他腳步遲緩地走到「天璇」星位,跪下。
「你是債務的橋樑,」陳玉娟將一把小刀遞給他,「需要你的血,連接過去與現在。」
陳文雄接過刀,手在顫抖。他看向林秀月,眼神裡滿是絕望的歉意。
「快點,」陳玉娟催促,「子時正刻只有一炷香的時間。」
陳文雄咬緊牙,用刀刃劃破左手掌心。血滴落在石灰畫的星線上,瞬間被吸收——不是滲透,是真的被「吸收」,石灰上的血跡消失得無影無蹤,彷彿那條線是活物。
陳玉娟滿意地點頭,點燃第三盞、第四盞燈。房間現在有四盞幽藍火苗在跳動,它們的光不向外散射,而是詭異地向內凝聚,聚焦在林秀月身上。
林秀月開始感到拉扯。
那不是物理上的拉扯,而是從靈魂深處傳來的、一種被鉤子勾住慢慢拖拽的感覺。她的意識依然清晰,但感覺自己正在被「分層」——表層是此時此刻坐在這裡的她,底層是某種更本質的東西,正被那股力量往外抽。
「抵押之物,報上你的名,」陳玉娟的聲音變得空靈,像從很遠的地方傳來。
「林秀月,」她回答,聲音比想像中穩定。
「生年?」
「民國六十八年五月。」
「母親之名?」
「林麗華。」
每回答一個問題,拉扯的力量就增強一分。林秀月感覺到額頭冒出冷汗,但她強迫自己保持坐姿。她需要時間,需要等到陳文雄行動,需要等到小瀚的聲音——
陳玉娟點燃第五盞燈。她開始吟唱一種古老的調子,不是閩南語也不是國語,音節破碎而詭異,像是某種失傳的儀式語言。隨著吟唱,她手腕上的「未」字刺青開始發光——不是反射燈光,是從皮膚底下透出的、暗紅色的微光。
林秀月的視野開始晃動。她看見房間的牆壁在融化,不是真的融化,而是某種視覺扭曲。牆面上浮現出模糊的人影——一個年輕男人和一個年輕女人,手牽著手,那是陳玉娟的哥哥和她的阿姨。他們的影像很淡,像隔著毛玻璃,但確實在。
「兄長,」陳玉娟對著男人影像說,「通道即將打開。你等待的緣分,今晚就能續上。」
男人影像緩緩點頭。他的目光轉向林秀月,眼神裡沒有惡意,只有一種深沉的渴望——對圓滿的渴望。
第六盞燈點燃。
拉扯的力量驟然加劇。林秀月悶哼一聲,身體前傾,幾乎要倒下。她感覺自己的五感正在被剝離:視野縮小成隧道狀,聽覺只剩下陳玉娟的吟唱,嗅覺只剩下那古怪的燈油味。觸覺也在消失,她幾乎感覺不到自己坐在冰冷地板上的肢體。
這就是靈魂被抽離的感覺嗎?
「媽媽!」
小瀚的哭喊聲從隔壁房間傳來,尖銳而恐懼。
林秀月即將渙散的意識猛地一震。
第二幕|願力碰撞
房門被粗暴撞開的巨響。
陳文雄抱著小瀚衝進來,孩子在他懷裡掙扎哭喊,小手拼命伸向林秀月。陳玉娟的吟唱戛然而止,她猛地轉身,臉上第一次出現驚怒交加的表情。
「你怎麼——」
「夠了,玉娟姊!」陳文雄嘶吼,眼淚混著汗水流下,「夠了!放過他們!我來承擔!什麼都我來承擔!」
「愚蠢!」陳玉娟的聲音尖銳刺耳,「儀式已經開始,不能中斷!把他帶出去!」
但陳文雄不退反進,他抱著小瀚衝向林秀月所在的北斗陣中央。就在他踏入石灰星線範圍的瞬間——
房間裡所有的燈火同時瘋狂搖曳。
不是被風吹動的那種搖曳,而是像有無形的手在掐捏火苗,讓它們扭曲、拉長、縮短,在幽藍與暗紅之間急速變換。牆上的影子不再是人的形狀,它們膨脹、扭曲、糾纏在一起,變成某種多手多足、頭部畸形的怪物剪影。
林秀月感覺到三股力量在房間裡猛烈碰撞。
第一股是陳玉娟的執念之願——冰冷、堅硬、帶著二十年積累的瘋狂,像一根想要刺穿時空的鋼針。
第二股是她自己的母愛之願——溫暖、洶湧、不講道理地想要保護孩子,像一面不斷擴張的盾。
第三股是陳文雄的守護之願——混雜著愧疚、絕望、以及最後一刻的爆發,像一把想要斬斷一切的鈍刀。
三股願力都不是實體,卻在這個被儀式強化的空間裡具象化了。林秀月「看見」它們:執念之願是暗紅色的尖錐,母愛之願是金色的光暈,守護之願是銀白色的斷裂面。三者碰撞、摩擦、互相吞噬又互相排斥。
油燈的火舌暴漲,舔上天花板,卻沒有點燃任何東西,只是在那裡燃燒。熱浪撲面而來,但奇怪的是一點溫度都沒有——那是靈魂層面的「熱」。
陳玉娟額頭上的疤開始滲血。
不是慢慢滲出,是突然之間,那道淡粉色的疤痕裂開,暗紅的血珠一顆顆冒出來,順著她的鼻樑、臉頰滑落。她沒有擦拭,反而張開雙臂,聲音因為用力而撕裂:
「完成它!必須完成它!哥哥——」
牆上男人影像的動作加快了。他伸出手,不是伸向林秀月,而是伸向她身後的某個點——那裡空間開始扭曲,出現一個旋渦狀的黑暗洞口。洞口裡傳來嗚咽的風聲,還有隱約的、像是無數人同時低語的雜音。
林秀月感到自己靈魂被拉扯的那個「鉤子」,突然變成了無數個。它們從那個黑暗洞口中伸出,纏繞住她的意識,要將她整個拖進去。她知道,一旦被拖進去,她就會變成契約所說的「橋樑」——一個沒有自我、只供兩個靈魂通過的通道。
小瀚的哭聲更響了。
「媽媽!媽媽你在哪裡!我看不見!」
孩子的眼睛被願力碰撞的光影遮蔽,他只看見一片混亂的色彩和扭曲的影子。但他的聲音,他純粹的恐懼和呼喚,穿透了一切雜音,直抵林秀月意識的最深處。
就在這一刻——
林秀月睜開眼。
她的眼睛裡燃燒著從未有過的光芒。那不是反射燈火,而是從靈魂深處迸發出的、屬於「林秀月」這個存在本身的光。
「不,」她說,聲音不大,卻清晰地壓過了所有雜音。
她舉起手。
不是對抗的姿勢,不是推拒,而是張開手掌,對著那股拉扯她的力量——
握住了。
第三幕|契約改寫
時間在那一刻凝固了。
不,不是真正的凝固,而是林秀月的感知進入了某種超速狀態。她「握」住的不是實體,而是那股願力本身的流向——陳玉娟哥哥對來世姻緣的渴望,阿姨未竟的承諾,陳玉娟二十年的執念,以及這份契約本身累積的「重量」。
她感覺自己手中握著一條冰冷的、滑膩的、不停扭動的「繩索」。繩索的另一端連接著那個黑暗洞口,連接著兩個等待了二十幾年的靈魂。
而她的這一端,連接著她自己,連接著小瀚的哭聲,連接著陳文雄絕望的守護。
「這份契約,今天到此為止,」林秀月說。
然後,她用力折斷。
不是折斷手中的「繩索」,而是折斷了那份契約最核心的邏輯——抵押品必須被動接受處置的邏輯。
她將自己的意志,自己的「生之願力」,像最熾熱的鐵水一樣灌注進那條繩索。不是要摧毀它,而是要重鑄它。
陳玉娟發出淒厲的尖叫。她額頭的疤完全裂開,血流滿面,但她仍然試圖維持儀式。「你不能——契約是神明見證的——」
「那就讓神明看看,」林秀月站起來了。她的身體在發光,不是刺眼的光芒,而是溫和的、如同晨曦的金色光暈,「看看這份契約,到底應該是什麼樣子。」
她看向牆上男人的影像。
「你很愛她,對嗎?」她輕聲問。
男人影像遲疑地點頭。
「她也愛你,所以寧可終身不嫁,」林秀月繼續說,「但愛不是債務。愛不應該變成纏繞後代二十幾年的詛咒。」
她手中的「繩索」開始變色。從暗紅變成暗金,再從暗金變成清澈的、如同水流般的透明。
「如果你們真的想要來世的緣分,」林秀月說,「那我祝福你們。但這份祝福,不應該用任何人的犧牲來換取。它應該是自由的、純粹的、來自一個見證者的真心祝願。」
她鬆開手。
那條透明的「繩索」沒有斷裂,而是輕柔地飄向男人影像,環繞在他和女人影像的手腕上,形成一道淡淡的光環。
「我,林秀月,自願給予這份祝福,」她宣告,「不是因為契約強迫,不是因為我是抵押品。而是因為我理解了你們的遺憾,我願意用我的善意,願你們在該相遇的時候,能夠認出彼此,能夠不再錯過。」
黑暗洞口開始閉合。
嗚咽的風聲減弱,低語聲消失。洞口的邊緣發出柔和的白光,像黎明的天色。
男人影像看向林秀月,深深鞠躬。女人影像也同樣行禮。然後,他們牽著手,走向那個正在閉合的洞口。在完全消失前,男人回頭看了一眼陳玉娟,眼神複雜——有關切,有歉意,也有釋然。
洞口閉合了。
房間裡驟然安靜下來。
七盞油燈的火苗恢復了正常的橘黃色,穩穩地燃燒。牆上扭曲的影子消失,只剩下一室正常的、隨著火光搖曳的人影。
陳玉娟跪倒在地。
她臉上的血還在流,但她的眼神空洞,彷彿剛才被抽走的不是哥哥的靈魂,而是她自己生命的支柱。她手腕上的「未」字刺青不再發光,只是一道普通的墨跡。
「結束了?」陳文雄顫聲問,還緊緊抱著小瀚。
林秀月身上的光暈漸漸散去。她感到一陣強烈的虛弱,幾乎站立不穩,但她強撐著走到小瀚面前,從陳文雄手中接過孩子。
「沒事了,媽媽在這裡,」她輕聲說,撫摸小瀚的頭髮。
小瀚的哭聲漸漸平息,他睜大眼睛看著母親,小手抓住她的衣領。「媽媽……那個紅紅的阿姨好可怕……」
「她不可怕了,」林秀月看向跪在地上的陳玉娟,「她只是……太累了。」
第四幕|塵埃落定
警察在十分鐘後趕到。
帶隊的是負責小瀚失蹤案的張警官,他看到房間裡的景象——七盞油燈、石灰陣圖、滿地血跡、失魂落魄的陳玉娟——愣住了。
「這是……」他看向林秀月。
「綁架案,」林秀月平靜地說,她已經將小瀚交給陳文雄,自己站在警察面前,「陳玉娟女士綁架了我兒子,我們追蹤到這裡,制伏了她。她情緒不太穩定,可能需要醫療協助。」
她選擇了最簡單、最能被理解的解釋。願力、契約、靈魂通道——這些東西說出來只會被當成瘋話。
陳玉娟被警察扶起來時,沒有反抗,也沒有說話。她只是呆呆地看著虛空,偶爾喃喃自語:「結束了……真的結束了……」
張警官安排女警員帶她去清洗臉上的血跡,並叫了救護車。他走到林秀月身邊,低聲問:「陳太太,你確定不需要去醫院檢查?你看起來很虛弱。」
「我沒事,」林秀月搖頭,「我只想帶孩子回家。」
「我們需要錄口供,但可以明天再做,」張警官點頭,「孩子先帶回去吧,這幾天辛苦了。」
離開那棟老房子時,天邊已經泛起魚肚白。陳文雄開車,林秀月抱著小瀚坐在後座。孩子很快睡著了,呼吸平穩,小手還抓著母親的手指。
「秀月,」陳文雄從後視鏡看她,「你剛才……那是什麼?你怎麼做到的?」
林秀月低頭看著小瀚的睡臉,沉默了很久。
「我不知道,」她最終說,「也許是母愛的本能。也許是……當一個人被逼到絕境時,靈魂會自己找到出路。」
「契約真的解除了嗎?」
「我不知道,」林秀月誠實地說,「但我感覺……不一樣了。那份契約本來是冰冷的、強制性的東西。我把它變成了……一份祝福。自願的祝福。性質完全不同了。」
她看向窗外漸亮的天空。「陳玉娟的哥哥和阿姨,如果真的有來世,也許真的會因為這份祝福而早點相遇。但這不再是債務,而是禮物。沒有人需要為此犧牲。」
陳文雄握緊方向盤。「那玉娟姊她……」
「她失去了生存的意義,」林秀月輕聲說,「二十年來,完成契約是她活著的全部理由。現在契約以這種方式『完成』了,她需要找到新的理由活下去。但那不是我們的責任了。」
車子駛入市區,街燈一盞盞熄滅,早起的店家開始拉起鐵門。平凡的一天即將開始,對大多數人來說,這只是又一個尋常的早晨。
但對林秀月一家來說,漫長的噩夢終於結束了。
三天後,他們接到張警官的電話。陳玉娟在精神鑑定中被判定有嚴重妄想傾向,需要長期住院治療。她沒有對綁架指控提出異議,只是反覆說:「契約完成了,我可以休息了。」
小瀚恢復得很快。孩子似乎不記得太多細節,只說「紅紅的阿姨帶我去一個舊房子,說要玩遊戲,但遊戲不好玩」。他額頭上多了一個淡淡的紅色印記,不是傷疤,更像是胎記,就在眉心正中央。醫生檢查後說沒有異常,可能是壓力引起的皮膚變化。
但林秀月知道那是什麼——那是契約祝福留下的痕跡,是她與那份跨越兩代的緣分之間,最後的連結。
一個月後,他們再次去了北帝君代天府。
這次不是去借發財金,也不是去還願。他們只是去上香,感謝神明——無論那是什麼形式的神明——讓這件事有了結局。
林秀月在香爐前站了很久。她想起十二年前在這裡簽下的那張借據,想起副本上消失的名字,想起陳玉娟站在陳文雄身後的樣子。然後她想起自己握住那股願力時的感覺,想起那對靈魂牽手離開的背影。
她點燃三炷香,深深一拜。
心裡沒有願望,只有平靜。
離開時,阿惠姐叫住了她。
「秀月,」阿惠姐的眼神裡有種瞭然,「事情結束了?」
「結束了,」林秀月點頭。
阿惠姐從攤位下拿出一個小紅包,塞到她手裡。「給孩子壓驚。裡面是廟裡求的平安符,開過光的。」
林秀月接過,道了謝。轉身要走時,阿惠姐又說了一句:
「有時候,結束也是開始。你改變了一些東西,那些東西會繼續改變別的。緣分是連鎖反應,善意也是。」
林秀月回頭看她。「阿惠姐,妳到底知道多少?」
阿惠姐笑了笑,那笑容裡有歲月的智慧,也有一絲疲憊。「我賣金紙四十年,看過太多人來來去去。有些人帶著願望來,有些人帶著債務來,有些人……像你一樣,帶著改變的力量來。」
她頓了頓,補充:「你阿姨如果知道,會感謝你的。你給了她一個更好的結局。」
林秀月眼眶一熱。她點點頭,沒有再問,轉身離開。
走出廟埕時,陽光正好。小瀚跑在前面,陳文雄在後面追,喊著「慢點」。孩子笑得開心,那場噩夢似乎真的遠去了。
林秀月站在陽光下,感受著溫暖落在皮膚上。
她想起陳玉娟手腕上的「未」字刺青。
未完成。但現在,完成了。
以一種沒有人預料到的方式。
她低頭看著自己的手腕,那裡什麼都沒有。但她知道,有些東西已經刻在更深的地方——不是刺青,不是疤痕,而是一種理解。
理解到願力的雙面性:它可以成為纏繞的詛咒,也可以成為流動的祝福。關鍵在於,握著它的人,選擇用什麼樣的心去對待它。
「媽媽!快來!」小瀚在前方喊。
林秀月抬起頭,微笑。
「來了。」
她邁步向前,走向陽光,走向等待她的家人,走向這個剛剛重新開始的、平凡而珍貴的生活。
身後,廟宇的香火繼續裊裊上升,承載著無數人的願望與故事,在天空中緩緩消散,成為這座城市日常風景的一部分。
【第五集 ‧ 終】
後記: 多年後,林秀月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,遇見一對年輕情侶。男孩額頭有淡疤,女孩手腕有「未」字刺青,但他們笑得很幸福,說是在一次廟會中一見鍾情。林秀月沒有打擾他們,只是遠遠看著,心中默念:「祝福你們。」然後轉身,融入人群。緣分的連鎖,就這樣悄悄傳遞下去。
贊贊小屋小說作品集:
紅衣還願、大太陽奇遇記、未來列車、三年後的妻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