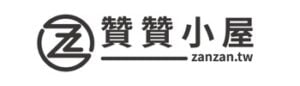(小說)紅衣還願4:債務人到抵押品的人格轉換
林秀月在廟中直面紅衣女人,得知自己才是被抵押的核心。舊契約真相揭開,孩子只是利息。母親選擇反擊,以自身願力迎向正月十五的對決。

第一幕|香爐前的灰
廟門在清晨六點開啟,第一炷香的煙還未升起。
林秀月和陳文雄站在正殿門檻外,手裡各自握著紅絲線的一端。絲線褪色得幾乎看不出原來的紅,像一道乾涸的血痕,繫著兩代人的願與債。
殿內值班的老廟公看了他們一眼,沒有多問。這幾天來找孩子的那對夫妻,廟裡的人都認得了。他低頭繼續擦拭供桌,動作緩慢,彷彿在給他們時間。
林秀月走進殿內,直接跪在北帝君神像前的蒲團上。陳文雄跟在她身後跪下,但膝蓋碰地時輕微一晃,像支撐不住身體的重量。
她沒有點香,也沒有擲筊。直接從口袋裡掏出打火機。
「秀月,」陳文雄低聲說,聲音發顫,「我們要不要先拜一拜,跟神明說一聲——」
「神明早就知道了,」林秀月打斷他,「十二年來,祂一直看著。」
她點燃打火機。火苗在昏暗的殿內跳動,將兩人的臉映得明滅不定。她將紅絲線的一端湊近火焰。
絲線沒有立刻燃燒。它先是捲曲,然後冒出細細的白煙,煙的氣味很奇怪——不是布料燃燒的焦味,而是一種陳舊的、類似檀香混著鐵鏽的味道。
終於,火舌舔上了絲線。
就在這時,殿外傳來不緊不慢的腳步聲。
林秀月沒有回頭。她專注地看著火焰沿著絲線蔓延,將那條纏繞二十幾年的信物一寸一寸吞噬成蜷曲的焦黑。陳文雄卻猛地轉頭,整個人僵住。
腳步聲停在門檻外。
「我以為你們會等到正月十五。」
女人的聲音平穩,甚至帶著一絲愉悅。
林秀月將最後一截燃燒的絲線丟進香爐,看著它在香灰上化為一撮灰燼。她這才緩緩轉身。
陳玉娟站在殿門口的晨光裡。
她穿著暗紅色的外套,不是鮮豔的正紅,而是那種接近褐色的暗紅,像乾涸已久的血。頭髮整齊地束在腦後,露出完整的額頭——眉心偏右的位置,一道淡粉色的豎疤在晨光下泛著微光。她看起來四十多歲,面容普通,唯有那雙眼睛異常清明,清明得近乎冷酷。
她的左手隨意垂在身側,手腕內側一個小小的刺青隱約可見。林秀月看清了那個字:「未」。筆劃簡單,卻像一道烙印。
「陳玉娟,」林秀月站起身,直視她,「我們來談條件。」
陳玉娟微微一笑,笑容很淺,只牽動了嘴角。「條件?你拿什麼跟我談條件?」
「放了我兒子,」林秀月向前一步,將香爐裡的灰燼捧起一把,撒向空中。細灰飄散,落在供桌、蒲團、以及她們之間的地面上。「我來抵。用我的命,換小瀚回來。」
陳文雄想站起來,卻踉蹌了一下。「秀月!不行——」
陳玉娟的笑意更深了。她走進殿內,腳步輕得像貓。晨光隨著她的移動斜斜切進殿內,將空間分割成光與暗的兩半。
「可是啊秀月,」她停在林秀月面前三步遠的地方,聲音輕柔得像在說一個秘密,「你從來就不是債務人。」
她頓了頓,欣賞著林秀月臉上瞬間的茫然,然後繼續說:
「你一直都是……抵押品。」
殿內的香燭同時晃了一下。
第二幕|未完成的契約
「什麼……意思?」陳文雄的聲音乾澀。
陳玉娟沒看他,目光始終鎖在林秀月臉上。「你阿姨當年跟我哥哥立下的,不是普通的婚約。那是一份『續緣契』。」
她從外套口袋裡掏出一張對折的紙。紙張泛黃脆化,邊緣殘破,但上面的毛筆字依然清晰。她將紙攤開,展示給他們看。
紙的上方用朱砂寫著三個字:續緣契。
內容是文言,但大意可辨:
text
立契人陳建邦(兄)、林秀英(姨),因緣份淺薄,此生難成連理。 今於北帝君前立誓:願以血親為抵押,換來世姻緣早成。 抵押者:林秀英之胞姊所出第一女。 若違此誓,抵押之物歸陳家所有,任其處置。
下方有兩個簽名、兩個手印,以及一個日期——民國六十八年三月。
林秀月盯著「抵押者:林秀英之胞姊所出第一女」那行字。胞姊所出第一女……她母親是阿姨的姐姐,她是母親的第一個女兒。
「你阿姨和我哥哥感情很深,但八字相剋,算命說強求會出人命,」陳玉娟的聲音平靜得像在講別人的故事,「他們不甘心,就想了這個辦法——用下一代的緣分,換這一世的相守。你阿姨答應,如果她這輩子無法嫁給我哥哥,就把她姐姐未來的第一個女兒『抵押』給我們家,作為來世姻緣的擔保。」
「荒唐……」林秀月喃喃。
「荒唐嗎?」陳玉娟收起契約,「但你阿姨確實嫁不了我哥哥。訂婚後三個月,我哥哥車禍走了。你阿姨大病一場,之後終身未嫁。契約的第一個條件實現了:此生難成連理。」
她走向神像,抬頭看著北帝君垂視的眼神。「按照契約,接下來就該是『換來世姻緣早成』。但怎麼換?需要儀式,需要媒介,需要……足夠強烈的願力來推動這個跨越生死的約定。」
「所以你們盯上了我,」林秀月說。
「不是『盯上』,」陳玉娟轉過身,「是『接收』。你是契約裡寫明的抵押品,從出生那一刻就註定要為這個約定服務。只是我們需要一個合適的時機,一個能讓願力最大化、足以撼動緣分的時機。」
陳文雄終於掙扎著站起來,臉色慘白。「十二年前的發財金……」
「是一個引子,」陳玉娟點頭,「我需要一個陳家的男人——血緣越近越好——來承接這份契約的『債權』。文雄,你父親臨終前應該告訴過你,你們家欠我們家一份情。那份情,就是我哥哥當年救過你父親的命。父債子償,天經地義。」
「所以妳找上我,要我借發財金,其實是……把契約的債務轉移到我身上?」陳文雄的聲音在顫抖。
「對。發財金的願力很純粹,『求安穩、求度過難關』。這和契約的本質——『求緣分安穩、求度過生死難關』——是相通的。用發財金做媒介,可以讓契約的願力附著上去,變成一筆可追索的『債務』。」陳玉娟耐心解釋,像老師在教學生,「而你,文雄,作為債務人,自然有權處置抵押品——也就是你的妻子,林秀月。」
林秀月感覺到一陣冰冷的麻痺從腳底蔓延上來。「處置……什麼意思?」
陳玉娟看向她,眼神裡終於有了一絲類似憐憫的情緒。「契約規定,若違此誓,抵押之物歸陳家所有,任其處置。你阿姨到死都沒有完成儀式來『換來世姻緣』,這算違誓。所以抵押品——你——的所有權,轉移到了陳家。而我,作為陳家現在唯一的直系血親,繼承了這份權利。」
她停頓,讓每個字都沉入空氣:
「我可以決定你的命運,秀月。從十二年前開始,就可以。」
第三幕|利息的真相
殿內陷入長長的死寂。
廟公不知何時已經離開,也許是感覺到氣氛不對,也許是陳玉娟事先打點過。整座正殿只剩下他們三人,以及高高在上的神像。
「那為什麼……」林秀月艱難地開口,「為什麼是小瀚?既然妳有權利處置我,為什麼要帶走我兒子?」
陳玉娟笑了。這一次,笑容裡有種疲憊的狂熱。
「因為我試過了,秀月。我試過直接執行契約。」
她捲起左手的袖子,露出手腕上方的一截小臂。上面佈滿了細密的、淺白色的疤痕,排列整齊,像某種儀式留下的痕跡。
「這些年,我用了各種方法想啟動契約,把你『處置』掉,讓我哥哥的靈魂能憑依這個契約找到轉世的通道,和你阿姨再續前緣。但每一次都失敗。願力不夠,或者說……抵押品本身的『抵抗』太強。」
陳玉娟放下袖子,看向林秀月的眼神複雜。「你活得太用力了,秀月。你對文雄的感情,對小瀚的愛,對這個家的執著——這些都是強大的『生之願力』,它們抵銷了契約的『死之願力』。我動不了你。」
「所以妳轉向小瀚,」林秀月明白了,「因為孩子更脆弱,連結也更深。」
「不只是因為脆弱,」陳玉娟搖頭,「而是因為小瀚是『契約生效後』出生的孩子。他是這份債務的『自然滋息』。在法律上,債務產生的利息,債權人當然有權收取。在願力的世界裡,道理是一樣的。」
她走向香爐,用手指撥弄那些紅絲線的灰燼。
「帶走小瀚,有兩個目的。第一,削弱你的『生之願力』。孩子是你的軟肋,失去他,你的生命力會大幅減弱,對契約的抵抗也會降低。第二,小瀚本身可以作為一種……催化劑。」
「催化劑?」陳文雄的聲音嘶啞。
「孩子的魂純淨,願力容易附著。如果我能在正月十五那天,用小瀚的魂完成一個儀式,就能強行啟動契約,把你,秀月,徹底轉化為『緣分的橋樑』。」陳玉娟說得很平靜,彷彿在說明天的天氣,「到時候,你就不再是你了。你會變成一個通道,讓我哥哥和你阿姨的靈魂能夠相遇、結合,在來世早早結為夫妻。」
「那秀月會怎樣?」陳文雄問。
陳玉娟沉默了幾秒。「橋樑用完之後,通常就沒有價值了。」
「妳要殺了她……」陳文雄的聲音開始顫抖,不是恐懼,而是憤怒,「就為了一個荒唐的契約,為了一個死了二十幾年的約定——」
「那不是荒唐的契約!」陳玉娟的聲音第一次尖銳起來,「那是我哥哥活著時唯一的念想!他那麼愛你阿姨,愛到寧可用下輩子的緣分來換這輩子的幾年!他死了,這份愛沒有死!它變成了債,變成了必須完成的約定!我是他妹妹,我有責任替他完成!」
她的呼吸急促,額頭上的疤微微發紅。「你們懂什麼?你們這些活著的人,整天計較柴米油鹽,計較孩子成績,計較房子貸款!你們根本不懂什麼叫真正的承諾!什麼叫跨越生死的約定!」
殿內回蕩著她的聲音,漸漸平息。
陳玉娟閉上眼,深吸一口氣,再睜開時又恢復了平靜。「所以你們看,秀月,你不是債務人,你是抵押品。小瀚也不是無辜的孩子,他是債務產生的利息。一切都是按照契約走的,很公平。」
「公平?」林秀月終於開口,聲音冷得像冰,「用一個我出生前就簽下的、我完全不知情的契約,來決定我和我兒子的命運,這叫公平?」
「契約就是契約,」陳玉娟說,「簽了字,畫了押,在神明面前立了誓,就要遵守。你阿姨遵守了——她終身未嫁。現在該你們遵守了。」
林秀月看著眼前這個女人,看著她眼中那種混合著執念、瘋狂、以及某種扭曲責任感的熾熱。她忽然明白了:陳玉娟不是壞,她是被困住了。被困在二十幾年前的那份契約裡,困在對哥哥的承諾裡,困在一個早已不該存在的約定裡。
但理解不等於原諒。
「小瀚在哪裡?」林秀月問。
「在一個安全的地方,」陳玉娟說,「正月十五之前,他不會有事。我還需要他保持純淨。」
「如果我答應配合妳呢?」林秀月向前一步,「如果我自願成為妳說的『橋樑』,妳能不能放過小瀚?讓他回來,過正常的生活?」
「秀月!」陳文雄抓住她的手臂。
陳玉娟仔細打量她,像在評估一件商品的真偽。「你願意?」
「只要小瀚平安,」林秀月說,「我願意。」
「但契約的啟動需要催化劑,」陳玉娟說,「沒有小瀚的魂,儀式可能失敗。」
「用我的,」林秀月毫不猶豫,「我的魂,我的命, whatever you need. 放過我兒子。」
陳玉娟陷入沉思。她走到神像前,抬頭凝視良久,然後轉身。
「有一個辦法,」她緩緩說,「但風險很大。如果你自願獻出自己,作為橋樑,理論上可以跳過催化劑的步驟。但這樣一來,橋樑的強度可能不夠,我哥哥和你阿姨的靈魂可能無法完全結合,契約只能部分完成。」
「部分完成會怎樣?」
「你依然會死,或者說,會失去自我,變成一個不完整的通道,」陳玉娟說,「而我哥哥和你阿姨的來世緣分,可能只能實現一半——也許他們會相遇但無法相守,也許會相守但充滿磨難。這違背了契約『姻緣早成』的承諾。」
她停頓,目光銳利地看向林秀月:「即使這樣,你也願意?」
「我願意,」林秀月說。
「不!」陳文雄擋在她面前,面向陳玉娟,「用我。我是債務人,我應該來承擔。用我的魂,我的命,放過他們母子。」
陳玉娟搖頭。「契約寫得很清楚,抵押品是『林秀英之胞姊所出第一女』。只有她符合條件。你,文雄,只是債務的載體,不是契約的核心。」
她看向林秀月:「如果你真的願意,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。但一旦開始,就不能停止。你會感受到……劇烈的痛苦。靈魂被抽離、被重組的痛苦。而且沒有回頭路。」
林秀月推開陳文雄,直視陳玉娟的眼睛。「我要先見小瀚。確認他平安。」
陳玉娟猶豫了一下,點頭。「可以。但只能你一個人來。文雄不能跟。」
「秀月,不要——」陳文雄想抓住她,但林秀月避開了。
「在哪裡見?」她問。
「跟我來,」陳玉娟轉身走向殿外。
第四幕|抵押品的覺醒
陳玉娟的車是一輛普通的灰色轎車,停在廟後巷子裡。林秀月坐上副駕駛座,陳文雄追出來,但陳玉娟已經發動引擎。
「地址給我!」陳文雄拍打車窗,「至少告訴我你們去哪——」
車子駛離巷口,將他的身影拋在後視鏡裡,越來越小。
車內很安靜,只有引擎的低鳴。陳玉娟專心開車,沒有說話。林秀月看著窗外流逝的街景,突然開口:
「妳手腕上的刺青,為什麼是『未』字?」
陳玉娟瞥了一眼自己的左手腕。「未完成。我哥哥和你阿姨的緣分未完成,這份契約未完成,我的任務……也未完成。」
「妳不累嗎?」林秀月問,「背負別人的約定二十幾年。」
陳玉娟握著方向盤的手微微收緊。「這不是別人的約定。這是我哥哥的遺願,是陳家的責任。」
「但妳的人生呢?」林秀月轉頭看她,「這二十幾年,妳只為了這份契約而活嗎?沒有自己的感情?沒有想過為自己而活?」
沉默在車內蔓延。很久之後,陳玉娟才低聲說:
「我愛過一個人。在我哥哥去世後第三年。但他害怕我們家的事,害怕這種……糾纏不清的債務。他離開了。那之後我就明白了,我的命運已經和這份契約綁在一起。完成它,是我活著的唯一意義。」
她的聲音很輕,輕得像在自言自語。
車子開出市區,往郊區的山路駛去。經過一段蜿蜒的道路後,停在一間獨棟的老舊平房前。房子周圍是荒廢的庭院,雜草叢生,看起來很久沒人居住。
「這裡是我哥哥以前的工作室,」陳玉娟熄火,「他喜歡在這裡畫畫。死後,這裡就空著了。」
她下車,林秀月跟上。
房子裡瀰漫著灰塵和霉味。客廳空蕩蕩的,只有幾張覆蓋白布的家具。陳玉娟帶她走到後面的房間,推開門。
房間被改造成一個臨時的臥室。小瀚躺在床上,蓋著被子,睡得正熟。他的臉色紅潤,呼吸平穩,看起來就像在家裡午睡。
林秀月衝到床邊,顫抖的手輕輕碰觸孩子的臉頰。溫熱的,柔軟的。小瀚動了一下,喃喃說了句夢話,又沉沉睡去。
「我每天給他餵飯、喝水,讓他按時睡覺,」陳玉娟站在門口,「我沒有傷害他。我需要他保持健康、純淨。」
林秀月彎腰,額頭輕輕抵著小瀚的額頭,閉上眼。這八天來,她第一次感覺到孩子真實的體溫,第一次確認他還活著。
「謝謝妳,」她低聲說,不知道是對陳玉娟說,還是對神明說。
她直起身,轉向陳玉娟。「什麼時候開始儀式?」
「明天,」陳玉娟說,「需要準備一些東西。今晚你就留在這裡陪他吧。這是最後一夜了。」
林秀月點頭。她在床邊的椅子坐下,握住小瀚的手。
陳玉娟看了她一會兒,轉身離開房間,輕輕帶上門。
夜深了。
林秀月坐在黑暗中,聽著小瀚平穩的呼吸聲。她的手始終握著孩子的手,像要將這觸感刻進靈魂裡。
窗外傳來輕微的聲響。她抬頭,看見陳文雄的臉貼在窗玻璃上——他不知怎麼找到了這裡,也許是跟蹤,也許是猜到了。
林秀月輕輕放下小瀚的手,走到窗邊,推開窗戶。
「秀月,」陳文雄壓低聲音,眼眶通紅,「我報警了,警察在路上了。你再撐一下——」
「不要,」林秀月搖頭,「文雄,聽我說。如果警察來了,陳玉娟可能會傷害小瀚,或者帶著他逃走。我們不能再冒險了。」
「可是你要答應她那個儀式!你會死的!」
「也許不會,」林秀月說,聲音平靜得連她自己都驚訝,「我一直在想。契約寫的是『抵押之物歸陳家所有,任其處置』。但它沒有說,抵押之物不能反抗。」
陳文雄愣住。
「我是抵押品,但我是活生生的人,」林秀月繼續說,思路越來越清晰,「我有自己的意志,自己的願力。陳玉娟說我的『生之願力』太強,抵抗了契約。那如果……我不只是抵抗呢?」
「什麼意思?」
「如果我不只是被動地抵抗,而是主動地……改寫契約呢?」林秀月的眼睛在黑暗中發亮,「契約的本質是願力。陳玉娟的哥哥和阿姨的願力,陳玉娟執念的願力,還有我的願力——願力是可以抗衡、可以談判的。」
她回頭看了一眼熟睡的小瀚。
「明天儀式開始時,我會全力反抗。不是用恐懼反抗,而是用更強大的願望去對抗。我要許願——願小瀚平安長大,願這個荒謬的債務徹底了結,願所有被這個契約束縛的靈魂得到自由。」
陳文雄抓住窗框,手指發白。「但那太危險了!萬一你輸了——」
「那至少我試過了,」林秀月微笑,笑容裡有種解脫的平靜,「文雄,這十二年,你一個人背著這個秘密,很累吧?對不起,我沒有早點發現。」
陳文雄的眼淚滑下來。「該說對不起的是我……我應該告訴你,我應該反抗——」
「明天,」林秀月打斷他,「明天儀式開始後,我需要你幫忙。陳玉娟說儀式需要我的自願,那表示過程中我的意志很重要。如果你在附近,如果你能讓小瀚醒過來,如果他叫我的名字……也許能給我力量。」
陳文雄用力點頭。「我該怎麼做?」
「躲在附近,等儀式開始。陳玉娟會專注在我身上,那時你找機會進來,叫醒小瀚。然後……然後就交給願力吧。」
窗外傳來遠處的狗吠聲。陳文雄知道自己該走了,否則可能被陳玉娟發現。
「秀月,」他最後一次握住她的手,「無論發生什麼,我愛你。這十二年,每一天都是真的。」
林秀月點頭,眼淚終於落下。「我知道。我也愛你。現在快走吧。」
陳文雄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。
林秀月關上窗戶,回到床邊。她俯身,在小瀚額頭上印下一個吻。
「明天,媽媽會保護你,」她輕聲說,「無論用什麼方式。」
她在椅子上坐下,閉上眼,開始在心裡積蓄力量。不是憤怒,不是恐懼,而是純粹的、母親的願望——願孩子平安的願望。
夜還很長。
明天,一切將見分曉。
【第四集 完】
贊贊小屋小說作品集:
紅衣還願、大太陽奇遇記、未來列車、三年後的妻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