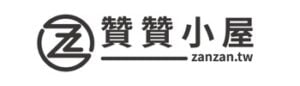(小說)紅衣還願3:兩個家族未清的舊債與願力
林秀月追查紅衣女人的來歷,發現小瀚早已多次與她接觸。家族舊債、願力轉移逐一浮現,正月十五逼近,母親決定主動反擊,在廟裡終結這筆代價。

第一幕|沉默的協議
陳文雄那三秒的凝視,在空氣中凝結成一道無形的牆。
林秀月沒有追問「她來過我們家多少次?」或「小瀚見過她嗎?」。這些問題的答案已經寫在丈夫崩潰又緊閉的表情裡。她彎腰撿起掉在流理臺上的菜刀,用水沖洗,用抹布擦乾,放回刀架。每一個動作都精準、緩慢、沒有顫抖。
「今晚我睡小瀚的房間,」她說,聲音聽不出情緒。
陳文雄張了張嘴,最終只吐出一個字:「……好。」
小瀚的房間維持著他失蹤那天的樣子。床上的被子亂捲成一團,書桌上有畫到一半的恐龍圖,地上散落著幾輛玩具車。林秀月沒有整理,她只是坐在床沿,目光掃過房間的每一寸。
那個女人來過這裡。
這個認知像冰水漫過脊椎。她來過這個家,可能坐過這張床,可能碰過這些玩具,可能和小瀚說過話。而陳文雄知道,卻選擇沉默。
林秀月閉上眼,開始在記憶裡搜尋。不是搜尋「陌生的紅衣女人」,而是搜尋「任何曾出現在這個家裡、額頭有疤、手腕有刺青的女人」。親戚?陳文雄的同事?快遞員?社區清潔工?水電維修師傅?
沒有。至少在她有意識的記憶裡,沒有。
但「沒有」反而更可怕。這意味著那個女人來的時機,可能是她不在家的時候。可能是陳文雄請假在家的某個週間下午,可能是她晚上去超市採買的那一小時,也可能是她回娘家的某個週末。
她起身,開始仔細檢查房間。不是警察那種搜證,而是一種更私密、更直覺的檢視。她拉開小瀚的書桌抽屜,翻看他的圖畫本。大部分是恐龍、機器人、飛機。但在最後一本的某一頁,她停住了。
那頁畫著三個人:一個高大的藍色人影(爸爸),一個矮小的粉色人影(媽媽),中間是小小的黃色人影(自己)。但在畫面的角落,用棕色蠟筆輕輕塗了一個模糊的、站在門邊的身影。那個身影沒有五官,但頭上畫了幾道紅色的線條。
像是紅色的頭髮?還是紅色的衣服?
小瀚從未提過這個「門邊的人」。林秀月翻到前一頁、後一頁,都沒有類似的圖。只有這一頁,多了這個模糊的存在。
她拿著畫本走出房間。陳文雄還坐在客廳沙發上,燈沒開,整個人陷在黑暗裡。
林秀月把畫本攤開在他面前的茶几上,手指點著那個棕色人影。「這是誰?」
陳文雄俯身看,肩膀明顯僵住。他看了很久,久到林秀月以為他不會回答。然後他低聲說:「……我不知道。」
「你說謊,」林秀月的聲音很輕,卻像刀刃。
「我真的不知道小瀚畫的是誰,」陳文雄抬起頭,在昏暗的光線中,他的眼睛裡有種絕望的真誠,「但我猜……可能是她。」
「她來的時候,小瀚在家?」
陳文雄點頭,動作沉重。「三次。第一次他兩歲,在睡覺。第二次四歲,在客廳看卡通。第三次……」他停頓,喉結滾動,「半年前。小瀚在房間玩,她說想看看孩子長得多大了,我沒讓她進房間,她只在門口看了一眼。」
「半年前,」林秀月重複。所以這不是陳年舊債突然啟動,這是持續的、長期的監視與等待。「她到底要什麼?」
「我告訴過你了,」陳文雄的聲音開始崩裂,「她要利息。發財金的利息。」
「但小瀚是在我們借錢五年後才出生的!」林秀月的聲音第一次揚高,壓抑的怒火混著不解,「那筆錢我們一年內就還清了!憑什麼五年後才出生的孩子,會變成利息?」
陳文雄的雙手摀住臉,聲音從指縫間擠出,嘶啞而絕望:
「她說……願力一旦成立,就像在土裡埋了種子。還錢,只是澆了一次水,讓種子不會枯死。但種子會一直活著,會往下扎根。」
他抬起頭,淚水爬滿臉龐,眼神卻空洞得駭人。
「只要願力的『根』還在,這片『土地』……」他顫抖的手指劃過空氣,指向腳下,指向這個家,「……這片用願力換來的安穩生活裡,長出的任何果實,都屬於她。時間,由她來定。」
林秀月感覺一陣冰冷的噁心感湧上喉頭。「所以……不是『一年還款期內』,而是……只要她還沒說停,願力就永遠有效?」
「對,」陳文雄的聲音輕得像灰燼,「她說,願力的期限,由債主決定。她說停,才停。」
「那她什麼時候才會說停?」
陳文雄沉默了很久。最後他說:「當利息被完整收走的時候。」
「完整地收走……」林秀月重複這句話,突然明白了,「小瀚的失蹤,不是結束。只是開始。」
陳文雄沒有否認。
林秀月後退一步,第一次用完全陌生的眼神看著丈夫。「所以你選擇相信她?相信一個能隨意定義期限、把我們兒子當利息的瘋子?」
「我沒有選擇!」陳文雄終於低吼出來,壓抑十二年的恐懼、愧疚、無力感全數爆發,「十二年!我每一天都在想有沒有別的辦法!我試過偷偷去廟裡解願,試過找道士,試過搬家!但每一次,只要我動了反抗的念頭,家裡就會出事——你記不記得你懷小瀚時差點流產?記不記得小瀚三歲那次高燒不退?記不記得我公司那筆差點讓我破產的官司?」
林秀月記得。每一個意外她都記得,但她從未把它們串聯起來。
「每次都是她出現,告訴我:『這是提醒。』」陳文雄的聲音嘶啞,「『遵守約定,他們就平安。』我能怎麼辦?秀月,你告訴我,我能怎麼辦?」
客廳陷入長長的死寂。
林秀月看著眼前這個崩潰的男人,這個她以為共同生活了十二年、卻獨自背負如此詛咒的丈夫。她該恨他嗎?該同情他嗎?還是該意識到,從十二年前他們走進那座廟開始,兩個人就踏進了不同的牢籠——她被蒙在鼓裡,活在虛假的平安中;他知情,卻被恐懼綁架,成了共犯。
「正月十五,」林秀月緩緩開口,「還有九天。」
「對。」
「她會在哪裡『完整收走』利息?」
「她沒說地點,只說時候到了,我會知道。」
林秀月點頭。她轉身走回小瀚的房間,關上門。
背靠著門板,她聽著客廳傳來壓抑的哭泣聲。但那哭聲很遙遠,像是從另一個世界傳來。她的大腦異常清醒,像被冰水澆過,所有的情緒都沉澱下去,只剩下一個核心:
不能等。
陳文雄選擇相信那個女人的「約定」,但她不能。一個能隨意定義願力期限的人,不可能在期限到時只是簡單地「收走」利息。正月十五很可能不是歸還日,而是某種儀式的完成日,是讓小瀚徹底變成「某種東西」的日子。
她必須在那之前找到那個女人。
而她唯一擁有的線索是:額頭的疤,手腕的刺青,紅衣,以及——她認識她。
第二幕|記憶的暗房
第二天一早,林秀月去了娘家。
母親正在廚房準備午餐,看見她來,愣了一下。「秀月?你怎麼來了?小瀚有消息了嗎?」
「還沒,」林秀月放下包包,「媽,我想問你一些事。」
「什麼事?進來說,外面冷。」
林秀月坐在客廳的舊沙發上,這張沙發她從小坐到大,絨布表面已經磨得發亮。母親端來熱茶,坐在她對面,臉上寫滿擔憂。
「媽,」林秀月握著溫熱的茶杯,「我結婚前,家裡有沒有……跟誰有過什麼債務?不是金錢的,可能是人情債,或者什麼約定?」
母親皺起眉頭。「怎麼突然問這個?都十幾年前的事了。」
「拜託,這很重要,關係到小瀚。」
聽到孫子的名字,母親的表情嚴肅起來。她想了很久,搖頭。「我們家一向簡單,你爸在世時也不愛欠人情。要說真的有什麼……就是你阿姨那邊的事了。」
「阿姨?」林秀月心頭一跳。母親的妹妹,她的阿姨,很多年前就搬去南部,很少聯絡。
「你阿姨年輕時,曾經跟一個男人有過婚約,後來那男人意外走了,」母親壓低聲音,「那家人有點……迷信,說你阿姨剋夫,要她賠償。賠的不是錢,是要她答應一件事。」
「什麼事?」
「具體我也不清楚,那時候你還在讀高中,」母親搖頭,「只記得你阿姨後來大病一場,好了之後就搬走了,很少回來。這件事我們也不提了,不吉利。」
「那個男人家裡,有什麼特徵嗎?」林秀月追問,「比如說,家裡的女人額頭有疤?或者手腕有刺青?」
母親猛地抬頭,眼神裡閃過驚恐。「你……你怎麼知道?」
林秀月的心沉了下去。「所以真的有?」
「那個男人的妹妹,」母親的聲音發顫,「我見過一次,額頭確實有疤,聽說是小時候受傷留下的。刺青……我不確定,但她是比較叛逆的那種女孩子。你問這個做什麼?秀月,這跟小瀚有什麼關係?」
「我不知道,」林秀月實話實說,「但我可能見過她。」
「不可能!」母親抓住她的手,「那家人在事情後就搬走了,聽說出國了。而且那都是二十幾年前的事了!」
二十幾年前。時間對得上。如果那個妹妹當年二十幾歲,現在就是四十幾歲,接近阿惠姐描述的年紀。
「媽,阿姨現在在哪裡?我能聯絡她嗎?」
母親的臉色變得很難看。「你阿姨……三年前走了。癌症。」
又一個線索斷了。
但林秀月抓住了一個關鍵:家族。如果那個紅衣女人是當年婚約對象的妹妹,那麼這筆「債」就不是從十二年前的發財金開始的。那筆發財金可能只是一個引子,一個讓舊債重新浮現的契機。
「媽,當年阿姨的那件事,有沒有留下什麼東西?信件?照片?」
母親猶豫了很久,最終起身走進臥室。幾分鐘後,她拿著一個舊餅乾鐵盒出來。鐵盒表面印著褪色的花卉圖案。
「這是你阿姨搬走前交給我的,說如果她有什麼萬一,就把這個燒了,」母親打開鐵盒,「但我沒忍心。」
鐵盒裡放著幾張黑白照片、一封信,還有一條褪色的紅絲線。林秀月拿起照片,第一張是年輕的阿姨和一個男人的合影,兩人站在廟前——正是北帝君代天府,只是建築看起來新一些。男人長相斯文,笑著摟著阿姨的肩膀。
第二張是團體照,裡面有阿姨、那個男人,還有幾個年輕人。林秀月的目光鎖定在角落的一個女孩身上。女孩大約十七八歲,穿著當時流行的襯衫長裙,但她的額頭——即使照片模糊,也能看見一道淺色的豎痕。
「這就是那個妹妹?」林秀月指著女孩。
母親點頭,眼神複雜。「她叫阿娟。陳玉娟。」
陳。和陳文雄同姓。
林秀月感覺一股寒意從腳底竄起。「她姓陳?」
「對,男方家姓陳,」母親沒注意到女兒的異樣,「怎麼了?」
「沒事,」林秀月強迫自己鎮定,拿起那封信。信紙已經泛黃,是阿姨的字跡,寫給母親的:
姊:
如果妳看到這封信,代表我已經不在了。有些債我還不了,只能帶走。但妳要小心,他們家的人很執著,說過的話一定會做到。當年我答應的條件,他們可能還會找別人討。尤其是秀月,她年紀正好……
信在這裡斷了,後面被撕掉了。
「後面呢?」林秀月抬頭。
「後面你阿姨自己撕掉了,說寫了不吉利,」母親嘆氣,「秀月,你到底捲進什麼事情裡了?跟媽說實話。」
林秀月無法說實話。她不能告訴母親,她的孫子可能被當成一筆二十幾年前舊債的「利息」。她只能搖頭。「我還不確定,媽。這個鐵盒能先借我嗎?」
母親擔憂地看著她,最終點頭。「你要小心。那家人……真的不太對勁。」
林秀月抱著鐵盒離開娘家。坐上車後,她沒有立刻發動引擎,而是再次拿起那張團體照,仔細看角落的陳玉娟。
年輕的女孩笑容靦腆,眼神清澈,完全看不出會變成一個能隨意定義願力期限、將孩子視為利息的追債者。但時間能改變太多東西,尤其是當一個人被「約定」與「執念」纏繞二十年後。
她翻到照片背面,有人用鋼筆寫了日期和名字。在「陳玉娟」旁邊,還有一行小字:
與兄長同願。
同願?什麼願?
林秀月想起廟裡的發財金,想起「願力債務」的說法。如果當年陳玉娟的哥哥和阿姨有過某種「願望」或「約定」,而那個約定因為哥哥的死亡未能履行,那麼這筆未償的願力,會不會轉移到妹妹身上?
而她,林秀月,因為嫁給了同姓陳的文雄,在某種扭曲的邏輯裡,成了「替代品」?
不,這太牽強。但所有的線索都指向這個方向:陳姓、額頭疤、二十幾年前的舊債、與廟宇的連結。
她需要確認最後一件事。
第三幕|刺青的形狀
林秀月開車來到阿惠姐的金紙攤位。今天廟埕人潮稍減,阿惠姐正坐在攤位後摺蓮花。
看見林秀月,她停下手,眼神裡有種「你果然來了」的了然。
「阿惠姐,」林秀月沒有寒暄,直接從鐵盒裡拿出那張團體照,指著陳玉娟,「是她嗎?十二年前那個紅衣女人?」
阿惠姐接過照片,戴上老花眼鏡仔細看。看了很久,她搖頭。「不像。照片裡這個太年輕,而且氣質不一樣。我說的那個女人,有種……尖銳的感覺。照片這個看起來很溫和。」
林秀月的心沉了一下。但阿惠姐接下來的話又讓她提起:「不過額頭的疤位置很像。都是眉心偏右,豎的。如果說是她老了以後的樣子……也不是不可能。」
「你記得她手腕的刺青是什麼樣子嗎?」林秀月追問,「哪怕一點點印象?」
阿惠姐閉上眼,努力回想。「很小,在左手腕內側。不是圖案,是字。一個字……筆劃很少,可能三四劃。看起來像『文』,又像『木』。光線暗,我沒看清。」
文?陳文雄的「文」?
還是……「木」?林秀月腦中閃過一個念頭。「是『未』嗎?未來的未?」
阿惠姐睜開眼,不太確定。「有可能。那個字的形狀……上面一橫短,下面一橫長,中間一豎穿下來。你說『未』,倒是有點像。」
未。未完成的「未」。未償還的「未」。未結束的「未」。
「阿惠姐,」林秀月深吸一口氣,「如果我給你看一個名字,你能不能回想一下,十二年前那個女人來廟裡時,有沒有被叫過這個名字?」
「你試試。」
「陳玉娟。」
阿惠姐皺眉,重複念了幾次。「陳玉娟……陳玉娟……不,沒印象。廟裡人來人往,我不可能記得每個名字。而且她當時沒有跟任何人交談,就是靜靜站在陳文雄後面,像個影子。」
影子。這個形容讓林秀月背脊發涼。
「不過,」阿惠姐突然想起什麼,「有一次,不是十二年前,是更早……大概二十幾年前吧,我還在跟我媽學摺金紙的時候,廟裡發生過一件事。有個年輕男人來還願,還的不是錢,是一條紅絲線。他說願望實現了,但代價太大,他要把『願』還給神明。」
「後來呢?」
「廟方當然不收,說願力一旦成立就不能還,只能償,」阿惠姐說,「那個男人就在香爐前跪了一整天,最後是被一個女孩子扶走的。那個女孩子……額頭好像也有疤。」
「記得那個男人的名字嗎?」
阿惠姐搖頭。「太久遠了。但我記得那個女孩子哭得很傷心,一直說:『哥,我們不要了,我們回家。』」
哥。
陳玉娟的哥哥。
所有的碎片開始拼湊:二十幾年前,陳玉娟的哥哥與林秀月的阿姨有婚約,兩人可能共同許下某個願望(或許與婚姻、家庭、未來有關)。願望實現的過程或結果導致哥哥死亡,阿姨大病。妹妹陳玉娟認為願力有代價,且代價未償,這筆債轉移到她身上。
十二年後,陳玉娟找到同姓陳的陳文雄——也許是巧合,也許是她刻意尋找的「替代品」——在他借發財金時介入,將自己的名字從借據副本上抹去(或許是為了切斷林秀月的連結,讓債務只在陳姓之間流轉),並定下「利息」的約定。
而現在,利息到期了。
「阿惠姐,」林秀月問出最後一個問題,「如果一個人想解開這種『願力債務』,除了找到債主,還有別的方法嗎?」
阿惠姐沉默了很久。最後她說:「秀月,有些債不是用來還的,是用來了的。要了,就得去當初許願的地方,把願力的根源挖出來。但那樣做很危險,因為你挖的不只是自己的願,可能還連著別人的命。」
「北帝君代天府,」林秀月說,「所有的根源都在那裡,對嗎?」
「對,」阿惠姐看著她,眼神悲憫,「但你一個人去沒用。許願的是兩個人,了願也得兩個人。缺一個,願力就散不掉,債就會一直傳下去。」
兩個人。她和陳文雄。
或者,更早之前:陳玉娟的哥哥,和她的阿姨。
第四幕|完整的代價
林秀月回到家時,天已經黑了。
陳文雄坐在客廳,沒開燈,電視也沒開。他就那樣坐在黑暗裡,像一尊逐漸風化的石像。
林秀月打開燈,將鐵盒放在茶几上,打開,拿出照片和信。她沒有說話,只是把這些東西推到他面前。
陳文雄低頭看。當他看到陳玉娟的照片時,整個人劇烈地顫抖了一下。
「你認識她,對吧?」林秀月平靜地問,「不是這幾年才認識,是更早。在我嫁給你之前,你就認識陳玉娟。」
陳文雄的嘴唇顫動,沒有聲音。
「讓我猜,」林秀月坐在他對面的沙發上,聲音冷靜得像在分析別人的故事,「陳玉娟是你遠房堂姊?還是同宗不同房的親戚?你們陳家當年有某種約定,要互相照應,尤其是對那些『背債』的族人。所以當她找上你,要你幫忙完成一筆二十幾年前的舊債時,你無法拒絕。」
「不是無法拒絕,」陳文雄終於開口,聲音沙啞得可怕,「是我不敢拒絕。我父親臨終前告訴我,我們家欠陳玉娟他們家一條命。具體什麼事他不肯說,只說如果有一天玉娟姊來討,我要盡力幫忙。」
「所以十二年前,她來找你,說需要一個『陳姓男子』的名義去借發財金,好讓願力債務的連結轉移到你身上?」
陳文雄點頭,眼淚無聲滑落。「她說,只要借據上有我的名字,債務就會轉移。她還說,這樣做對你也有好處,因為債務轉移後,原本可能落在你身上的厄運就會消失。我信了……我真的信了。」
「但借據上本來有我的名字,」林秀月說,「是你簽完後,她要求去掉的,對嗎?」
「對。她說,這樣才能確保債務完全轉移,不會波及到你。她說這是保護你。」
「保護我,」林秀月重複這三個字,突然笑了,笑聲裡滿是荒謬,「所以你們一起騙我去簽名,然後偷偷把我的名字從副本上抹掉。你們讓我以為自己是共同借款人,實際上把我排除在債務之外——但同時,卻把我的兒子當成利息?」
陳文雄雙手摀住臉,肩膀劇烈起伏。「我不知道會這樣……她當時只說需要一個孩子『掛名』在願力之下,這樣願力才能延續。她說不會真的對孩子怎麼樣,只是需要一個形式上的連結……我以為等小瀚長大,離開家,連結自然就斷了……」
「但她沒有告訴你,連結會在七歲時收緊,」林秀月替他說下去,「她也沒有告訴你,正月十五不是歸還日,而是願力完全轉移、孩子徹底成為『利息』的完成日。對嗎?」
陳文雄的哭聲停了。他抬起頭,臉上滿是絕望的醒悟。「你……你怎麼知道?」
「因為我開始用腦子思考,而不是用恐懼,」林秀月站起身,「陳文雄,我們沒有九天了。每多等一天,小瀚和那個女人的連結就深一分。等到正月十五,就算她說『利息收完了』,小瀚也不再是我們的孩子了。他會變成某種……願力的容器,一個永遠被綁在那筆債上的東西。」
「那我們該怎麼辦?」陳文雄也站起來,眼神裡終於有了迫切,「去找她?但她在哪裡?十二年來,她只在我需要見她的時候出現,我從來不知道她住哪裡、怎麼聯絡!」
「我們不去找她,」林秀月說,「我們去廟裡。去當初許願的地方,把這件事了結。」
「可是阿惠姐說——」
「阿惠姐說,許願的是兩個人,了願也得兩個人,」林秀月打斷他,「二十幾年前許願的是陳玉娟的哥哥和我的阿姨。他們都不在了。但債務轉移後,新的債務人是陳玉娟和你。而你是用我們夫妻的名義去借的發財金,所以我也被捲進來了。現在,了願需要的是我們三個人:你、我,和她。」
「她不會出現的,」陳文雄搖頭,「她一定會等到正月十五。」
「那就逼她出現,」林秀月從鐵盒裡拿出那條褪色的紅絲線,「用這個。阿惠姐說,當年陳玉娟的哥哥想還願,還的就是一條紅絲線。這應該是某種信物,代表那個未完成的願望。如果我們在廟裡公開燒掉它,她一定會來阻止。」
陳文雄看著那條紅絲線,眼神恐懼。「但如果她來了,卻不是來談判,而是來加速呢?如果她當場就要完成『收割』呢?」
「那就讓她帶走我的,」林秀月平靜地說,「我是當年被排除在借據外的人,但也是小瀚的母親。如果願力債務需要一個生命來了結,我來替。」
「不行!」陳文雄抓住她的肩膀,「絕對不行!」
「那你有更好的辦法嗎?」林秀月直視他的眼睛,「等九天,然後眼睜睜看著小瀚變成願力的一部分?還是我們現在就去,把這件事做個了斷?」
陳文雄的手緩緩鬆開。他低下頭,看著茶几上陳玉娟年輕的照片,看著那個笑容靦腆、額頭有疤的女孩。二十幾年的時間,可以把一個人變成什麼樣子?
「好,」他終於說,「我們去。什麼時候?」
「明天,」林秀月說,「大年初三已經過了,廟裡人會少一些。我們一開門就去,在北帝君面前燒了這條紅絲線,然後等她。」
「如果她不來呢?」
「她會來,」林秀月肯定地說,「因為這條絲線燒掉,願力的『根』就斷了。她二十幾年的執念也會散。她不會允許這種事發生。」
那天晚上,兩人沒有再交談。林秀月依然睡在小瀚房間,陳文雄睡在主臥。但半夜時,林秀月聽見客廳有動靜。她輕輕打開門縫,看見陳文雄跪在神龕前——那裡供奉著一尊小小的北帝君像,是當年還願時從廟裡請回的。
他沒有點香,只是跪著,低聲說著什麼。林秀月聽不清全部,只捕捉到幾個詞:
「……怪我……保護他們……最後一次……」
她關上門,背靠著門板,閉上眼。
腦中浮現的卻是小瀚的臉。不是失蹤後這八天她反覆回憶的那張笑臉,而是一個更早的畫面:小瀚三歲時,有一次發高燒,她整夜抱著他,用毛巾擦他滾燙的身體。天快亮時,燒終於退了,小瀚睜開眼,用沙啞的小聲音說:「媽媽,我夢見一個紅紅的阿姨,她說我很快就可以一直玩了。」
當時她以為是孩子發燒的囈語。
現在她知道,那不是夢。
那個紅紅的阿姨,從那時起就已經在等待了。
林秀月握緊手中的紅絲線。絲線很舊,幾乎一扯就斷,但它承載的願力(或詛咒)卻纏繞了兩個家庭、兩代人。
明天,她要親手燒了它。
無論代價是什麼。
【第三集 完】
贊贊小屋小說作品集:
紅衣還願、大太陽奇遇記、未來列車、三年後的妻子。